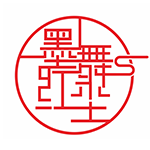小时候,最初听姥姥说她的名字叫王凤英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严凤英。因为严凤英唱的黄梅戏,姥姥时常念叨。姥姥说严凤英嗓音甜美,扮相也好。我问姥姥啥是个扮相。姥姥就说:“可怜的娃,连个黄梅戏也没看过。好扮相就是女人的俊模样嘛。”我似懂非懂,懵懂中感觉,好扮相就是好看。
我觉得,能够叫“凤英”这个名字的人,首先要有一副“好扮相”,尤其是眼睛,百看不厌——当然,我这样说的根据是来自姥姥——我小时候就总喜欢盯了姥姥的眼睛看。看着她的眼睛,我就心安,就心里暖和;其次,心眼儿十分好。我自小就确立了这样的看法,而且,只是自个儿心里想,从来没有跟人说起过。连姥姥也不知道我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我已经不记得姥姥一开始跟我讲她名叫王凤英的时候,那是哪一年。总之我很小。应该是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是1971年之前,1967年之后。这中间的四、五年,大部分时候,我跟随姥姥省城乡下两头住。很可能就是这四、五年之间的某一天,有意无意中,姥姥告诉我她叫王凤英。究竟是不是在我的询问之下她才告诉我的,已经无从查考。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姥姥名叫王凤英。王凤英姥姥并不是识文断字的人,她仅仅认得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以及像“大”“小”“田”、“天”“日”“人”等少数字,还是沾了扫盲的光,但是她却给她的大外孙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夏冰。这个叫夏冰的外孙长大后,就用这个名字写文章,先是小说,后来是诗歌,然后是散文。由县里到市里,再到省城,再到全国,再到网络。于是,天南地北有很多人知道我叫夏冰。但是他们大概以为这个名字只是我随意起的、是为了上网才起的一个名字。很少有人会想到,没有姥姥王凤英,就没有她的外孙叫夏冰这回事。
一开始听姥姥说她名叫王凤英时,我十分惊奇。因为我眼里的姥姥已经是个老太太。尽管那时候姥姥也就是个四十大几五十来岁。我觉得一个老太太与“王凤英”这样俏丽的名字不大般配。没有什么原因,真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凤英”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很美。这么说不是说姥姥不美。毕竟,用美来形容一个老太太,在一个小孩子眼里,有些滑稽。这种滑稽、新奇的感觉在我心里存在了很长时间。只要我意识到姥姥叫王凤英,心里就会这么想。我是说王凤英这个名字,恰好是姥姥的名字。这件事情真有意思。真奇怪。其实也不奇怪。究竟我是怎样习惯了、认可了、以至于喜欢了姥姥这个名字的,我好像不大容易说清楚。姥姥咋叫个这名字呢?这是一开始的念头。姥姥叫这样一个名字,真好。这是后来的想法。这个过渡的完成,似乎经历了一段时间。那些年,我和姥姥朝夕相处,按姥姥的话说,我就是她的肉尾巴。哪怕是她要到正房对面的南房抱柴禾,哪怕是她到东耳房里挖米面,我也要紧紧拽着她的后襟跟着去,等她抱上柴禾,或者挖上米面,我再拽着她的后襟跟回来。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这个过渡自然就完成了。所以到后来,“王凤英”和“姥姥”一关联,我心里就亮堂堂的。王凤英姥姥就有本事叫人心里亮堂堂,美滋滋。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一个冬天的晚上,姥姥取出一对靴子,对我说:“娃,看咱的毛靴。”我仔细一看,这靴子从靿子到身儿,全是用一指厚的灰色毡子做成的,靿子有半个小腿高。我问:“你取出它来做甚呀?”姥姥说:“我穿上它看电影去呀。”我这才知道晚上村里要演电影啦。是的,姥姥喜欢看电影。受姥姥影响,我也喜欢看电影。于是姥姥就穿上毛靴,套上棉袄,围上头巾,领上同样包裹得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我,去看电影。我们去了后,已经有不少人了。大家争着抢着占领“有利地形”。人是陆陆续续的来,抱孩子的妈,呼朋引伴的年轻人,前拉后扯的一家子,刚结婚的小两口,颤颤巍巍拄着拐杖相搀相扶的老头儿老太太……小孩子们东奔西跑,吱哇乱叫,一刻也不闲……整个电影场子里,哄哄嘈嘈,热闹非凡,真是比赶会也红火。看到半中间,电影场子里有不少人跺脚板。姥姥说人们冻得忍不住了。我问姥姥冻不冻。姥姥说不冻。姥姥问我冻不冻。我说不冻。等看完电影回到家里,姥姥脱下毛靴来,招呼我:“你摸摸,可热乎哩。”我伸手到靴子里头摸,真暖和啊。后来每逢冷天村里演电影,我便对姥姥说:“姥姥,穿上你的毛靴。”姥姥就呵呵地笑了。姥姥笑了以后,我不由自主就想起了她叫王凤英这件事,心里亮堂堂,美滋滋,感到很美很美,所以也就情不自禁笑了。
这件事说明,王凤英姥姥和夏冰外孙是多么的契合、投心。
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我是跟着姥姥在乡下度过的。那时候,姥爷在太原工厂上班,每年枣熟时节,我便跟随姥姥回到乡下老房子里。这所老房子,我十分喜欢。院子大,四合头房,正房前两株粗大的枣树。站在当院看,正房就像一个倒睡的“7”,西面宽,东面窄。“7”的顶头从北向南依次是灶间、大炕,“7”的后半部分是外间,外间还直通着东耳房。正房屋门就是开在外间的。里外间之间有一个门。正房地势比较高,屋门与院子之间,是一片砖墁地,全是用青灰色的方砖铺成的;房檐探到这砖墁地之外,这片空地方就像一座戏台——我小时候,常与邻舍孩子在上面唱歌、演样板戏。站在戏台上仰头看,顶头是斑驳、不齐整的栈板。麻雀常在里面住,小燕子也喜欢在上面垒窝。正房左右各有一个小屋,俗称“小耳房”。小屋前一片空地,我们叫它“小院子”。小院子里长着几株小枣树。那时候,我老爱在里面玩,冷不丁就被小枣树上的尖刺儿挂住了,扎破手、出了血,也是常有的事。不过这还不要紧,你忍一忍过几天也就没事了,要是挂烂了衣裳,那可了不得,勤谨仔细的姥姥,绝对不允许你胡乱糟蹋衣裳的。到那个时候,她倒是不大声嚷嚷,也不骂你,更不打你,只是板着个脸,让你自觉理短。我十分不愿意看到姥姥这副模样,所以在玩的时候,就比较自觉,不至于得意忘形、自由散漫到不知天高地厚的程度。
小时候,这所大房子就是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姥姥总是在大清早就起来,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于是,宽敞清洁的院子里,便是我们自由快乐的天地了。我们嘻嘻哈哈绕着枣树捉迷藏,小心翼翼到小耳房门前看野猫——一般是看不到的,要不就抓石子,跳格子,打三角,弹玻璃球,拿上木头的铁丝的或者纸做的手枪冲锋枪,分成“我军”“敌军”打仗,叠上纸飞机绕院子里飞……反正有无穷无尽的玩法,于是也便有了无穷无尽的欢乐。
姥姥整天不闲着。不是在缝纫机上缝补,就是坐在炕头搓麻绳,要不就坐在大门外巷口的石头上,一边纳鞋底,一边跟人唠嗑。
我喜欢看姥姥在缝纫机上做活儿时的情形。姥姥戴一副黑红色镜腿子的老花镜,镜片圆溜溜的,花镜的两条腿用一根细线连起来,套在脑后,花镜便松松垮垮地架在姥姥宽扁的鼻梁上,显得特别好笑。那缝纫机机头一端的轮子上上了一层红油漆,轮子转起来后,就形成一个红圈儿,我盯着这个红圈儿,目不转睛地看,姥姥就从眼镜上边看我,我更觉得可乐。有时候我不由得想动手去摸那个飞快地转着的红圈儿,姥姥就赶紧看着我,眼里流露出严厉的神色。我就知道这是不许可的事情,就不敢摸了。
到了晚上,姥姥也不歇着。那时候,因为姥姥省城、乡下轮流住,所以就没接电灯,而是点着一盏煤油灯。煤油灯是由灯瓶、灯杆、底盘组成,灯杆和底盘是一个高约尺余的木头架子,我们叫它灯树子。一到晚上,煤油灯下,姥姥一边“哧啦——”“哧啦——”地衲鞋底,一边摇晃着身子,轻声给爬在她腿上的我呢呢喃喃哼故事:“故事故,故事底下没人住,一住住下(哈)怪(个)老师父——坐起来,我的腿叫你压酸啦!”我爬起来,托着腮帮子,听她把这我已经听得烂熟的故事一直哼下去。我倒不是为了听故事,而是喜欢听她的声音,看她灯光下的脸。她的喃喃的声音温柔、亲切,她的被灯光映照着的脸庞发着淡淡的光彩。昏黄的煤油灯下,甜蜜的喃喃声里,一老一小紧紧依偎……

 姥姥名叫王凤英
姥姥名叫王凤英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