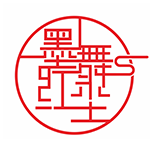初夏的一个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湛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墙外的杨柳越发显得青翠了,在和风中舒展着它那欲要滴出水的枝叶儿。天是好天唉!女人自言自语了一句,进屋继续翻腾一木制衣柜中的衣物。一件,一件,一会子功夫,半人高的衣柜就空了,衣物在炕上堆积成一座小山。女人拿起一件,展开来,仔细瞧上半天,平平铺在炕头,想叠,思索了半天,又放下,接着又拿过另外一件。衣物大多是男人的,有男人平日里常穿的西服,夹克,衬衫,冬日里的棉袄……当她摸出一件男人的红裤衩的时候,嘴角处不禁闪过一团笑,脸上浮出桃花一样的红晕。女人太清楚这件红裤衩了。男人将犯本命,女人也学着城里人的讲究,在赶集的时候,背着同行的几个女人偷偷专为男人买的,就连当时小贩的调戏语都记得:
红裤衩,质量好;能辟邪,平安保;
床上活,情趣高;穿上它,女人笑!
确实笑了,但不是女人。当晚,女人从包里掏出来递给男人的时候,男人憨笑着迫不及待的就爬上炕,三下五除二脱去衣裤,穿上了身。照男人的说法,他还从未穿过这么鲜艳的呢,当初结婚时,只不过身上搭过一床红绸缎而已,那不算穿。男人站在炕上抖了几抖腿脚,嬉笑着,说很合适,他要女人也上炕来。那晚,男人确实真的比以往要厉害很多,接连好多次,直到女人招架不住,苦苦哀求,男人方才罢休。
女人的思绪开始胡奔乱跑了。她想到了新婚那天,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咬她耳垂;想到了初识那次,男人趁她没防备把手伸进她的衣襟;更想到了男人出门前的头一晚,在她身上耍各种千奇百怪的花招……女人的心头热乎乎的,血脉跳动得很是厉害,她由不得自己,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身体僵在地上,条件反射性的轻咬住嘴唇,两只鼻孔里喘出别样的气来。
该死!过了半会儿,女人暗骂了一句。屋内空荡荡的,低低的声音显得很有分量,女人惊觉过来了,脸色变得很是难看。红晕退去了,换上的是腊月天的灰白,她紧咬了下牙齿,把手中的那条红裤衩甩得老远。红裤衩象飞碟样旋转着直直飞到门口放的一盆月季上,轻飘飘地搭了上去。裆部处正好不偏不倚地露出了一朵盛开的红花,象东方初起的太阳一样,和红云之间光辉相映。
月季是他们结婚后第二天栽培的。男人说,在花里,月季一年开花次数最多,他希望她也像月季一样,等他每次外出回来的时候,也开出姹嫣夺目的花朵。
女人前去踹了一脚花盆,她觉得实在憋屈。男人说过,每当月季开花的时候,他会准时回来,可花都开了好多天了,再等下去花都败了,男人的踪影在哪儿?别说踪影了,就是连捎个话儿都没见着。女人忘不了昨日,她亲眼见着,邻家的男人回来后,刚踏进大门,就将手中的提包往地上一丢,一把抱住了他的女人,疯狂啃吻起来。女人试想过很多种男人回来时的场面,一分一秒,一刻一时,她想得快要迷失了自我,男人成为她生活的全部,甚至是宗教。
花盆象个不倒翁晃动了几下,停止了。红裤衩落了下来,落在花盆旁的一滩水上,顷刻间,湿透了,红色不见了,变得黑乎乎的,象某个夜晚。对,是洞房花烛的那个夜晚。那晚,男人坚持要亮着灯,女人害羞,怎么也不肯,最后无法,男人用了一块红布包裹了屋顶上倒挂的那盏灯泡。在黑亮亮的光线的刺目下,女人强忍住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她记得,永远记得!
女人越想越气,最后眼里都泛起了浪花。他们结婚虽说已快三年了,可一起相处的日子扳着手指头都能算得过来。二十刚出头的女人,若是没结婚,还是一个童稚未尽的大姑娘呢,多么美好的年华啊。但时间是不会怜惜人的,走了就走了,谁也左右不了,就算用金山银山也换不回。狠心的男人啊,你就一点都不会怜惜你的女人吗?你在外面的花花世界里,不论你是在摸爬滚打,还是逍遥快活,你丢在家里的女人的韶华正在孤单寂寞中一分一秒的逝去,和流水一样,昼夜不息。
女人的眼湿透了,胸前的白衬衫也湿了一大片。湿漉漉的眼泪,是冰凉的,里面包装着男人的“甜言蜜语”。男人说,等他在外发了财,带她去南方。女人说,南方哪里?男人说,当然是苏杭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去西湖,去划船,去断桥,去雷峰塔,也当一回白娘子和许仙。女人轻吻着男人结实的胸膛甜蜜地笑了。男人的许诺为女人起初的等待增添了不少活气,但当光阴不断地挪移时,女人对生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生活,是生与活的组合,相爱的两个人如同这两个字一样,分开了,就变了意义了,女人和花一样,不是金银养护的,需要男人的爱来呵护。
该死的男人。女人呜咽着又咒骂了一句。泪干了,脸颊上印上了两道异常明显的痕迹,上头还有尘埃的存在,如同干巴巴的血渍。女人觉得全身一点力气都没了,绵软无力地蹲在台矶上,任凭金黄的太阳的芒照射,任凭不时吹来的风且夹杂着灰尘扑面。日头西下的时候,女人才反应过来,她全身酸痛,尤其是两只小腿,已经失去知觉很久了。
女人没有用晚饭就直径囫囵躺在了炕上。也不知睡去了多久,是摆钟的敲打声,把她惊醒了。夜好象很深了,又好象天将要亮了。窗外暗乎乎的亮——是“马虎子”月亮。唉,又要到孤枕难眠的时刻了。女人实在是睡不着了。摆钟再次敲了下时,一阵五音缺四音的歌声从老远传来,在夜中来回飘荡,回响,像嫠妇哭又像野狼嚎:
采呀下花呀黄了呀,我丈夫出了个门呀,
我的尕肉儿呀,相思病得下了,
一夜嘛睡不着……
女人努力了很久,才听得出是村里的老光棍三喜子。女人听出来了,三喜子喝醉了,更听出来了,三喜子想女人了。三喜子的声音到了女人的大门口停下了。只听得“咣当”一声大门被撞开的声响,一跌跌撞撞的脚步近了起来。女人心跳得突突的,她想喊,却总也喊不出来。女人情急之下,跳下了炕,用方桌抵住了门。
三喜子一边说着满嘴胡话,一边拍打门。女人不敢吱声,只顾全力压住方桌,深怕三喜子这个丑陋的老光棍“破门而入”。僵持了一阵子,三喜子不拍打门了,好像半躺在廊沿上了,身子依在门上,头时不时撞击下门,三喜子开始哭,哭得很伤心,很伤心。
女人明白,三喜子,四十大几的人了,还是光棍,可能他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到死也不会知道女人是什么滋味。女人有点心疼他了。此时此地,自己何尝不和三喜子一样,都需要不同于自己身体的人。女人颤抖着说,你甭哭了,门我是不会开的,你若愿意,我陪你说会儿话。三喜子问,啥话?女人小声说,你想说啥话就说啥话,今晚夕我都听。
同是天涯沦落人,只是相逢不对时唉!三喜子嘴里胡囔着,被憋了几十年的话东一搭西一搭没个头绪。女人笑了,还真是个旱鸭子。女人重新躺回到了炕上,她已过来人的身份一分一厘丝毫不落地“指点”三喜子。“马虎子”的月亮啊,真的,比圆月还要亮,只是这种亮,能使人迷糊具体的时光。女人真的迷糊了,她都开始分不清自己到底和谁在“亲密无间”,说着那种让人脸红耳赤的情话。等女人真切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发觉自己光着了身子,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宽大的炕上。门外的那个醉汉三喜子嘴里的胡话还在接连不断,不时还发出急促异常的呻吟声。
一种罪恶感涌上了心头。羞耻,愧疚,自责,全都来了,象鬼魅一样张牙舞爪,扭摆着缥缈不定的身子一股脑全朝女人袭来。女人发疯似的,没有任何规则的挥舞着双手,蹬着双腿,打啊,踢啊,唾骂声是又凄厉而又无力:滚,你给我滚……随着床单被罩撕破的声响,女人的呜咽和啼血鸟儿一样,吟唱,吟唱,在失落的夜里吟唱。
三喜子走了。世界平静了。女人也终于平静了。许久,许久,她脑袋里竟然出现了空白,谁也记忆不起来了。唯见透过窗缝的一道暗乎乎的光亮照在摆钟上,射出一朵隐约不可辨形的花朵,没有枝叶,也没有光彩,只有怨尤、寂寞、空洞。在屋内闪烁了一阵子,便消失匿迹了。

 相思病
相思病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