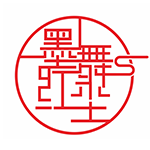月亮粑粑团,跟我到江南。江南弥陀寺,婆婆纺线子。
清脆的童谣在石板街陡然升起,惊飞沿街山墙破洞里的麻雀。皎洁的月光下,依稀可见这种家雀惊慌的剪影。天很青,云很淡,天上数不清的星星眨着眼睛,把稚气的童声传得很远。一群半糙子从南街跑到北街,又从老街疯到堤上,大声念着江南童谣,无意中把长辈移民生涯的秘密告诉了地,告诉了天。
老街不老,至今不过百多年。听老人说,还在男人留辫子的时代,这里只有一座南宋留传下来的弥陀寺,伫立于水洼遍地的一块高地中央。清末的虎渡巡阅司,从靠近长江的集生村迁到庙旁,才吸引四面八方的人,跟着月亮粑粑来到弥陀寺,逐渐形成一个热闹的集镇。小镇无名,就以香火鼎盛的寺庙当成镇名。如此说来,古云梦泽的浩渺烟波化为一马平川的江南沃野,只是眨眼前的事。至于弥陀寺改成弥市,则是解放后的事了。倒不是破除迷信,因为同县的观音垱、普济等镇名都没有改。我猜想,是当时的当权者,放不下对城市的向往。自己不能去城市,把居住地的地名加个市字,也可聊以弥补心里的缺憾。
这首童谣很美,勾起过我无限遐思。它是一副流动的画卷,让一轮冰清玉洁的月亮永远跟着我,一会儿爬上屋脊,一会儿挂在柳梢,使我心里涌出道不尽的温馨,说不完的诗意。童谣第四句的婆婆,指的就是邻居魏婆婆,她住我家后面,大门朝着羊叉古子。她每天白天弓着腰走进走出,在前后墙壁上贴满刚糊的鞋壳子,晚上则坐在手摇纺车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手摇纺车一手放棉条,把一根根洁白的棉条纺成一坨坨均匀的棉线。嗡嗡的纺车声,曾经把扎在母亲怀里的我,轻轻地送进香甜的梦中。
或许这支童谣不是特指魏婆婆,但在我的心里也是确凿无疑的认定了。这第四句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支持了我的看法。比如,江南弥陀寺,娘种菜园子。江南弥陀寺,爹卖米圆子.......就说米圆子,当时弥陀寺只一家卖。卖家姓陶,他的二儿子陶永才是我的同班同学。米圆子两分钱一小碗,三分钱一大碗。偶尔找母亲要上两分钱,陶伯总是给我多打一点,差不多赶上三分钱的了。一碗又烫又辣的米圆子下肚,心肝五脏都是热烘烘的,比现在吃麻辣烫还过瘾。
小镇是个农散集市,没有制造业,大多数人都是做小生意谋生,所以出现许多带老板姓氏的招牌产品。比如罗家发糕、郑家米酒汤圆、高家霉豆渣等。罗家发糕是我同学罗正贵家做的,又白又泡,一股米面的清香,不时逗引着路人肚子里的馋虫。郑家米酒汤圆是同学郑家才家里做的,路过他家大门,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回首一嗅,仿佛要把这米酒香带回家去,高家霉豆渣我经常去买,并不是因为高家的漂亮女儿高长翠是我同学,而是因为霉豆渣既便宜又好吃。辣椒炒霉豆渣,那滋味令人胃口大开。当然,在食物短缺的年代,任何有别于白菜萝卜口味的品种都能使人产生很强的食欲。高家没有门面,生产和销售都在一条小巷的深处。
一个冬日的傍晚,我拿着母亲给的五分钱,敲响了高家虚掩的大门,高长翠红红着脸从写作业的小桌旁过来,递给我两块霉豆渣。没有说话,我们那时男生和女生基本上不说话,她扑闪着大眼睛对我一笑,转身等我出去后又掩上大门。兔毛一样柔软的白色霉丝,在我手掌上蠕动,弄得手心痒痒的,我感到很温暖。可饥饿的肚皮不争气地咕咕鸣叫起来,不由加快了脚步向家里走去。沿街屋檐下喇叭传出的激昂语录歌,时而从前面,时而从后面灌进我的耳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让人觉得这里并不是一个偏僻的江南小镇,而是中国、而是世界。
突然,我看见一群因贪玩、迟迟还没有回家的同学迎面走来。有比我大,有比我小,没有同班同学。他们边在雪地打闹,边念着童谣:董存瑞、十八岁,参加了中国的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他的任务完成了......他们看到我在雪中踽踽独行,立即换了一首童谣,朝我齐声念到:
吃灰包,屙黑屎,上天去,雷打死,下地来,火烧死,躲在门旮旯里,鬼掐死!
我听了血往上冲,感到非常愤怒,那一副副熟悉的面孔,一瞬间显得那么陌生和可憎。但见他们人多势众,我最终低下头,想从街边闪过去。可初雪中的石板街有点打滑,人没摔跤,霉豆渣晃掉雪水里了。这首童谣明显是针对我的,针对我家的。在粮食节约年代,我家卖过灰包,在这个小镇,也只有我家卖过灰包。灰包是高粱成熟时期病变的产物,有人吃它、有人卖它都是无奈之举,它比野菜更难让人接受。当然,这是站在当时角度上的认识。如今野菜是保健佳品,灰包绝迹了,我相信如果还存在,也会正大名分地摆上餐桌。
我望着浸满雪水的霉豆渣愣住了,眼泪也不知不觉漫出来了。这两块霉豆渣是晚餐唯一的下饭菜,回家还不会被吵死?见闯了祸,这群孩子一哄而散,消失在各个门板后面和长街转弯处。只有一个高我一个年级的肖五星留下了,默默地拾起雪水中的霉豆渣。我想赔你,可我没钱。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知道刚才他并没有念那首侮辱人的童谣,但他与那些人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他住我隔壁,一道回家的路上,他爸在门口拦住我们,厉声问五星,你欺负了他了?五星畏畏缩缩地说没有,我也摇头。肖伯没仔细问缘由,只让我们进屋,然后严肃地对我们两人说,你们没有任何理由闹意见,只能互相帮衬,你们的出生是一样的,与其他人不能比。别人是祖宗三代逃荒来的,根正苗红,你们不是。
肖家是什么来历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父亲是四六年穿着国军军服退役来的。在运动中是死老虎,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单凭肖伯的话,我也对五星产生出一种亲切感。肖伯的意思,是让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能够抱团取暖。可惜的是,我和五星没有成为铁哥们,主要是我们都性格内向,又不在一个年级,不久后又不在一个学校了。
肖伯说话,我只有点头的份,但我心里还是不以为然。我为什么不能跟人比?我又不比别人少一根汗毛。每次开学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数学书上的习题全部做完了,我看的课外读物比语文书深奥广泛多了。能够代表我们年级语文水平的,只有罗正喜、刘以德和我三个人。当我逐渐意识到肖伯说的话是真理的时候,身心已经碰的支离破碎了。
肖伯和刘以德的父亲同在废品回收站上班。废品回收站对我来说,比图书馆和学校还重要。它不仅帮我找到帮贴家用的出路,而且成为我寻求知识的一条渠道,同时解决了我身体和精神的两重饥渴。我每次去卖破烂时,看见无数好书当成废品堆在墙角,既心痛又高兴,总是悄悄藏几本在衣袋里带回家。好多世界名著都是我读高小和初中时,在废品回收站偷的,从来没有露出破绽。过后回想,一个卖破烂的孩子,破衣里鼓出了几个大包,大人真没有察觉吗?显然不是,他们是在四面楚歌里,放知识一条生路;更是为一个求知的孩子,悄悄打开一扇窗子。
拾破烂,当地的说法是捡布巾子,当然就是以拾破布为主。至今我印象深刻,碎布九分钱一斤,卖出经验来了,就会从中剔出比巴掌大点的布片扎成捆,叫大布,价格翻一倍。收购站收到大布,则卖给魏婆婆一样的人贴鞋壳子用。拾到一件破衣裳,能撕出几块大布,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至于学习,那是随意。学校绝不会因为哪个学生成绩不好而开除他,连留级制度也废除了。不像现在的孩子,被应试教育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们的童年却被更厉害的饥饿撕得粉粹。在现今的同学会上,陶永才还在说,那时上课根本没心思听讲,只盼放学铃声响,赶快跑回家,看能不能抢在哥哥和弟弟之前进门,找到一点剩饭或者半个萝卜。拾破烂,扯马草是我的功课,星期天和寒暑假卖破烂和卖马草的收入,足以让自己不至于失学,成为人所厌弃的混混。但拾破烂跟要饭一样,让人特没有面子,一般都瞒着同学,独自走乡串街。在乡下,经常遇到恶狗挡道和顽童嘲笑。虎渡河对岸的雷州是我喜欢去的地方,因为不同县,不会遇到熟人。在那里,有一次,几个孩子跟了我几里路,并且不厌其烦反复唱着一首童谣:

 在老街成长
在老街成长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