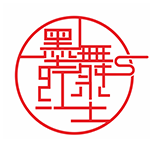1960年是三年经济困难最难熬的一年,那年年底,19岁的我从甘肃被调到新疆阿克苏,还在那里过了一个旧历新年。
岁月荏苒,斗转星移,一转眼就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虽然岁月的长河湮没了许多如烟往事,但在阿克苏过的那个春节却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年,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上正热火朝天建设着的酒泉钢铁公司,因为甘肃严重缺粮,突然接到了中央“下马”指令。为了保住这支队伍,以待粮食形势好转后重新上马,国务院冶金工业部决定将数万名职工向全国各地疏散,帮助疏散地建设那些尚未“下马”在建项目。并且明确只要疏散地安排口粮计划,人员工资仍由冶金部发放。
我们这支小股“部队”目的地是南疆阿克苏,那里正准备筹建一个大型棉纺厂。我们1000多人风餐露宿乘坐一长溜解放牌卡车辗转一个多星期才赶到那里(那时兰新铁路才铺通到一个叫柳园的小站,大部分路途靠汽车运输),一到那儿,就听说那个棉纺厂也接到了“下马”的指令,原因与甘肃一样,地方上严重缺粮,养活不了我们这一大批人。不过,这么多人好不容易过来了,时间又到了岁末,一时也没法转移到其它地方去,而且也不知道哪儿要我们,只能先住下来。有关部门要求当地政府临时给我们安排最低口粮标准,随便找点活儿让我们先干着。后来,我们就在那里滞留了三个多月。
地方上安排的口粮计划每人每月只有24斤,没一点副食品计划,也买不到一点蔬菜,市面上只有食盐不上计划。我们就像行军打仗似的,就地搭棚子办食堂。食堂里只有两口大铁锅,一口锅烙饼,一口锅烧水。每人每天就只能吃到用八两面粉烙成的两块饼。每天吃两顿,每顿供应一块饼和一小勺子开水。那一块用四两面粉烙成的大饼,因为又没法进行发酵,感觉个头并不大,好像一个人需要三四块才能吃得饱。由于燃料紧张,开水供应也是有计划的,每人发红、绿两块水牌子,早上打水时用红牌,晚上打水时再用绿牌换回红牌,第二天早上再用红牌换绿牌,如此循环往复,绝对公平合理,任何人都没机会多喝一口。喝的水是从几百米开外的一条大河里挑来的,那条河在地图上就叫阿克苏河,据说其源头在100多公里外的苏联境内(苏联解体后,那边的国家叫吉尔吉斯斯坦),河面虽不算宽,但水流还挺急,夹带着泥沙,像是黄河里的水。我们吃饭时,都是坐在自己的地铺上,一小口一小口地享受着那块十分珍贵的烙饼,一边用饼蘸一点掺了盐末的辣椒面,一边喝点儿像马尿似的“黄河水”。
安排我们做的工作是挑河。那条新开的河是个半拉子工程,已经挑了一半,民工全撤走了。我们用的工具全是当地发的,两个人抬一副柳条编成的筐,有专人装筐。谈不上有什么工效,干多干少没人管,当地没人过来,我们自己的带队干部也和我们一样,肚子饿得哇哇叫,哪有心思去抓工效?顶多是在工地上转一圈做做样子就回宿舍了。我们住的宿舍原是一家砖瓦厂的大厂房,室内空间特别大,一根根立柱支撑着硕大的屋顶,地上铺着一层稻草就是我们睡的地铺(这里与家乡江苏处于同一纬度,听说也种植水稻)。我们都将自己带去的行李卷儿摊在稻草上,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两个那样大的厂房,竟然装下了这支1000多人的逃荒大队,只是委屈了我们那几位随队领导,也不得不与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
那年农历闰六月,过春节时已是2月中旬。腊月廿九的那天下午,当地有关部门也给我们分配了一批春节特供副食品,我们找不到车往回运,只好派了几十个工人步行去市里背菜。记得我也被派去了,回来的路上我背了三十多斤大白菜,因为有十多里路,那天又特别暖和,背得浑身是汗。好在可以边走边吃生白菜,感觉到既充饥又解渴,舒服极了。真想不到那玩意儿还能当水果吃。背菜的人大都是背什么就吃什么,有时也互相进行品种调剂,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背的是洋葱,他跟我要了半棵大白菜同时给了我两个洋葱,虽然平时连切洋葱时都会辣得眼泪直流,但生吃起来倒也不觉得有多辣。不过,我这辈子也就吃了那么一次生洋葱。
大年三十的那顿年夜饭吃得特别早,其时,太阳还高高地挂在西天,为了那一顿丰美的大餐,大家都有点儿急不可耐了。主食还是那吃惯了的一张饼,另外每人分到了一小勺子土豆炖牛肉和两份分量极少的炒菜,确切地说仍然是吃了个半饱。开饭时,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把手还碰到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一个工人看到了炊事员给他打的牛肉土豆分量有我们的两倍多,就不客气地夺下了他的饭盒,放在食堂门前“展览”。那位领导原是酒钢水泥厂厂长,这回算是虎落平阳了,后来他气得连晚饭也一点儿没吃。年初一的那天,上午的那顿饭仍与上一天晚上差不多“丰盛”,晚饭就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了。
接下来又放了好几天的假,当地政府也并不需要我们干多少活,只是希望这些瘟神早点离开,好减轻一些地方上缺粮的压力。白天,偌大的宿舍里空空荡荡的,大家都像饿狼似的到处游荡。一个月几十元的工资大都不够用,因为在黑市上买一公斤地方粮票就得十多元。阿克苏街上有一家卖烤馕的店铺,老远就能闻到从那里飘散出来的诱人的香味,虽然一块馕只有几分钱,但因为要收100克粮票,多数人只能在门口闻闻香味,咽几口口水。馕是维吾尔族人的主食,有点像家乡的那种大圆烧饼,中间较单薄,周边有一道凸起的环,味道与烧饼差不多,也是用发过酵的面粉烤制的,记得好像是比烧饼少了一层芝麻。馕的烤制过程很特别,炉子是在地上挖的一个瓮形的圆洞,洞底燃着树柴火,贴饼子的人跪在地面上,样子很滑稽。那个馕店后来几乎耗尽了我们这些人的全部工资,有的人还将随身带过去的一些值钱的家当都卖掉填了肚子,听说有一位随队的领导将一块英纳格手表只卖了一百多元钱,买了十多公斤粮票。我也用一件只穿过两次的新卡其布中山装跟当地人换了两公斤粮票。那些日子,口袋里揣着两公斤粮票,好像比现在信用卡里存了上万元钱更觉得富有。
过了春节,就听到消息说,要将我们这一批人转移到北疆石河子去,有关部门正在落实转移的车队。后来因为车队迟迟落实不下来,我们在那里又“待命”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阿克苏河边上杨树已露出了新绿,桃花也正含苞欲放,春姑娘已经悄悄地来到了南疆大地。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天山北面,那里的早春还常常大雪纷飞。
这么多年过去了,听说阿克苏早就升格为地级市,旁边的那个叫温宿的小镇也升格为县城。真想在有生之年再能有一次故地重游,只怕是因为年岁渐长,关山远隔,这种奢望很难实现。

 在新疆阿克苏过年
在新疆阿克苏过年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