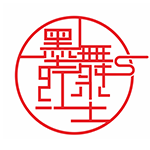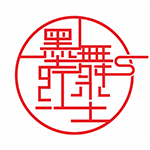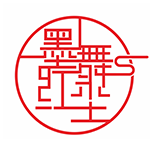某年秋天,老麦家的灶膛通不出气,烧不了火,他女人就骂骂咧咧带儿子回了镇上娘家。老麦让人带话给当初砌这灶台的泥瓦匠,泥瓦匠的女人说他一大早就去程三家修屋顶了。
傍晚,泥瓦匠带着程三家的酒气摇头晃头而来。
老麦独自坐在银杏下喝闷酒,矮桌上一壶酒,一只碗,几碟咸菜,一堆花生,半只咸鸭蛋,一张冷饼。酒壶碗著上落满昏黄的光线,扇状黄叶被风吹下来,掉在头顶,肩上,膝头,掸去又落下,没完没了。
增加碗著后,泥瓦匠坐于纷乱的落叶之中,掸去酒中不知名的小虫,呷了一大口黄酒。在酒来酒去,话进话出中,灶膛通不了气的原因不是老麦女人乱烧火,而是泥瓦匠技艺不行。
泥瓦匠闷头喝掉一碗酒,拍碎了酒碗,掌中鲜血让他兴奋难抑。
关于泥瓦匠技艺不行的轱辘话像风中秋叶,掸去又落下,没完没了。老麦的嗓音里停满了蜜蜂,密不透风的嗡嗡声前赴后继无尽无休马不停蹄,掌中鲜血像某个秘语向着泥瓦匠的脑中跑去,从脑中绕了一圈又跑回掌心,手就变成了铁拳头,像锤子那样朝着老麦不停发出嗡嗡声的脑瓜砸去,老麦立即就倒了下去,像桌椅碗箸那样毫无逻辑地散了架。
银杏叶纷至沓来,没完没了,仿佛掩盖一个秘密那样掩去老麦的耳鼻眼脸,泥瓦匠揭开一片落叶,微颤探老麦的鼻息,那里是无边的毫希望的寂静,老麦死了。
在临溪的栾树林躲了一夜的泥瓦匠,被微寒的晨露与黄色落花打醒,想起昨日之事,来自酒后的生猛早已烟消云散。他不敢返回村庄,沿溪朝东走去,溪水清浅,飘淌着云朵、鱼群、水草以及一些无法辨认形状的阴影,岸边芦荻蓬松寂静,水鸟单脚停留于水边小汀,溪中沙洲不知名的植物枝头缀满紫花。对岸乌桕林黄红叶间挂着黑色的种子,其下彼岸花开,虚幻而飘摇的红色无穷无尽,像他此刻的心情,恐慌却无力,晨雾从林中漫出来,眼前所见之物变得模糊而柔软。
走在渐渐扩大的晨雾中,泥瓦匠寒冷饥饿,想念着滚烫的白粥,又咸又鲜的腌笋,却不敢掉头。他往迷雾深处走去,微眯眼睛凭着水声沿岸而前,世界微蓝而寂静,仿佛梦境。他希望昨天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噩梦,迷雾散去,太阳出来,他从床上坐起,女人已在丝瓜架下摆好白粥和腌笋。笼着秋阳的黄色花朵上,蜜蜂来去,白蝶绕飞,细小的仔瓜挂在叶间,光线堆积在一切所见之物上,鸡群在碎影里啄食,鸭子被黄狗赶往荷塘,洗衣石上立着两只鹅,水中倒映一团白影。
他在溪水里清洗一双手,粗壮有力的大手曾是他的骄傲,现在成了他悔恨的源头。他朝着鱼群扔石头,鱼群一哄而散。他揉碎青草,摘下野花扔向水中,鱼群又聚集回来,他又捡起石头扔过去,然后对着溪水难看而笨拙地哭起来。
迷雾中有人喊他,一只眼,一只眼,大清早在水边嚎什么?你女人满世界找你,一早上敲开全村的门窗找你,说老麦家的灶膛通不了气,做不了早饭,急等你回去通膛,你倒在这嚎叫!
泥瓦匠听出迷雾中那人是村里的郎中,于是惊奇而小心地问,老麦已经起床了?
郎中大声说,今天是被他女人揪着耳朵起床的。然后又不怀好意地压声喊道,你赶紧回去给那女人通一通吧,否则今天全村都不得安宁。
老麦的早饭摆在银杏树下,清晨的光线穿过枝叶,照着碗里的白粥,碟中的腌笋。他戴着一顶不合时宜的草帽坐在阴影里,招手让泥瓦匠过去。咯吱咯吱嚼完一截腌笋,喝了一大口白粥后,老麦歇口哑嗓道,这是你女人送来的白粥,你也赶紧喝一碗,再把我屋里灶膛通一通。他把草帽压了压又道,今天不叫你喝酒了,昨天你喝点酒,醉得不成样,为哄你这酒疯,把我的喉咙都说哑了,好不容易才把你哄高兴,唱着《苏三起解》颠三倒四跌撞回去。泥瓦匠捧着粥碗,白口连着喝掉大半碗,他看着被碎影切割得面目模糊的老麦,嘿嘿干笑。
那天晚饭,女人温了一壶黄酒,被泥瓦匠推开,说了自己打死老麦又虚惊一场的事,他在灯下总结道:菩萨保佑祖宗显灵,昨天那只是一个恶梦,我晓得了,这是祖宗菩萨要我戒酒哪。
女人独自喝了半壶,支着筷子冷笑,放你妈的屁,过不了三天,还得喝上。你的十八代祖宗让你戒过多少次了,哪次你戒成?黄狗生了黑狗你说祖宗有话讲,母猪不下仔你说祖宗生气了,稻谷比隔壁程三家矮小你说祖宗在那边缺粮了,母鸡不下蛋,果树结果少,韭菜早开花,甘蔗不甜芝麻不长节……都是你祖宗来信了。
泥瓦匠就气得把剩下的半壶黄酒一仰脖子全喝光,然后呼呼大睡,梦里一顶草帽朝他缓慢飞来,像一艘充满危险的大船。
数日后,老麦病了。村里都在传,县城医生说他的病叫硬皮病,就是脸皮发硬,以后笑和哭都差不多了。于是,笑和哭差不多的老麦躲在家中不再出门,家中大事小事都由他女人说了算。
中秋刚过,泥瓦匠又被喊到老麦家,老麦戴着那顶不合时宜的草帽,在猪圈深处面无表情地等他,身后昏暗的光线里,一头母猪,七只猪仔,哼哼唧唧。老麦计划把猪圈挖深砌上砖块,铺上管道,通向水沟沿荷塘的水路排出村外,学城里猪场无稻草养猪法。泥瓦匠听着老麦上次为他搞哑的嗓子,不忍泼他冷水,进了猪圈说干就干。
天黑前,猪圈被挖出几米深的一个长方形坑道,四周砌上砖,看上去整整齐齐因果相连合缝合榫,泥瓦匠挺得意。但是,老麦围着深坑转了一圈之后却说,看上去像个墓地,放棺材刚好。泥瓦匠不接话,他扔下砖刀,爬上坑说,没力气了,明天再扫尾。
晚饭很快摆出来,银杏叶无风自落,不等人上桌,碗著饭菜上已经缀满扇形黄叶。泥瓦匠心中有气看什么都不高兴,诘问能不能把饭桌移出院外。老麦用上次的哑嗓干笑,银杏叶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好东西。喝过一碗滚烫的黄酒后,泥瓦匠不再生闷气,他总结无稻草养猪的可行性,值得全村推行,以后家家户户都砌坑,他的活干到腊月都干不完……。
老麦却给他泼冷水,说他技艺不行,砌个坑,像个棺材壳,明天他就砸了去镇里重新请个泥瓦匠。
泥瓦匠阴着脸喝渐渐凉去的黄酒,越喝越冷。老麦喝了酒,还是喜欢说车轱辘话,他敲着桌子恨铁不成钢地唠,痛心疾首地叨,捶胸顿足地为他惋惜,苦口婆心地为他规划未来,语重心长指出缺点,循循善诱点出长处……。一壶黄酒已经被泥瓦匠喝得见了底,老麦还在嗡嗡地指点江山,泥瓦匠捏碎了酒碗,鲜血满手让他兴奋难止,泥瓦匠晓得,他只怕是喝多了酒又要做噩梦,既然噩梦总会醒来虚惊一场,那就直接往心里的想法走去。
于是他的饱含鲜血的拳头又一次挥了出去,对面的老麦仿佛早已等候多时,只等拳到,就往后倒去,失去重心的泥瓦匠扑地晕了过去,像一段湿木头不再动弹。
泥瓦匠是被老麦的女人用一碗凉水泼醒的。女人说,老麦被他打死了。
但是她刚才看着银杏叶不断落下,前思后想,左思右虑后,想着人与这树叶一样迟早要落地,何况人死不能复生,也不想泥瓦匠吃子弹。
她说她一直想出去打工,老麦总不让她出门,现在只要泥瓦匠把老麦埋掉,再送她到渡口,回来告诉大家,是他泥瓦匠送他们夫妻上了船外地打工去,这件事就没人晓得,过个三年五载,她再抱个骨灰盒回家,就说老麦在外地得病不治而亡了。
老麦被埋进了那个新砌的像棺材壳一样的长坑里,泥瓦匠的心突突跳个不停,手脚发抖,就觉得老麦这死鬼有点过早发硬发冷,还有点发臭,像是死了很多天,但是他一句话也不敢出口。
夯实泥土后,老麦女人还细致地铺上稻草,一个新鲜干净的猪窝,母猪和七只猪仔重新回去哼哼唧唧。她说还是我们稻草养猪好,虽然臭气冲天,却是好肥料。临上船前,老麦女人嘱咐他好生养那一窝猪仔,可以卖个好价钱。

 【秋】银杏树下的秘密
【秋】银杏树下的秘密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