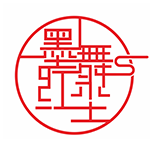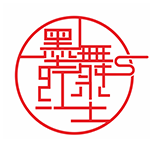个性签名:
| 标题 | 推荐 | 字数 | 阅读 | 评论 | 发布时间 |
| 画梦 |
|
1202 | 591 | 2 | 2014-10-04 |
| 小读书 |
|
4232 | 585 | 4 | 2014-05-10 |
| 【红尘有你】 一条河 陪着我们流 |
|
6263 | 717 | 6 | 2014-04-20 |
| 红尘有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
|
4705 | 590 | 7 | 2014-04-11 |
| 【红尘有你】谁使谁幸福 |
|
2620 | 5435 | 14 | 2014-04-05 |
| 不关门的梵高 |
|
3327 | 1107 | 2 | 2014-03-21 |
| 是谁把这个城市弄冷 |
|
2967 | 827 | 5 | 2014-03-21 |
给天澜留言
-
天澜 2014-03-21 08:05:48
是谁把这个城市弄冷
那家臊子面馆,从早到晚被阳光坚持的照着。那阳光是从对面高楼林立的建筑物的一个大缺口,侥幸投过来的,但光照时间真的很长,很有“关照”的意味。
挂着艳丽的彩珠帘子的小面馆,像一个很蕴藏能量的火柴盒。帘子挑开,胖女人从里面走出来,就像从里边取出一根干燥好使的大红头的火柴,只要有人走过,那火柴头就会热情的擦亮自己,发出一小团咄咄的暖光。
一度,我很迷恋这一片城里少有的阳光地带。
小面馆,其实是在我们小区右首的转弯处,我每天进进出出都要路过它。当然,每天还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理由或不需要理由的从它门前走过。走路的人,通常都这样:带着自己的腿,带着自己的影子,带着自己即得的心情和心思,以自己独一无二的走姿和体态,穿梭来兮在岁月的累加和日子的削减中。
如果这时候胖女人也正好从面馆走出来,这片被阳光格外青睐的地带就更加的亮豁起来。她会认真而热情的和每一个人打招呼。下班了?回来了?忙啥去?孙子接上了?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叫上名字或者称呼不上的,只要和她照上面了,这个面就不会让你白照。她笑的时候,宽宽的脸更宽的拓展开,两坨本就不打算躲藏的“山里红”就占据了脸庞最显眼的部位,直夺眼球。这就和她的声音一样,本来是亮亮爽爽的,但因为她那一口识别性很差的怪味方言,抢了人家耳朵的先,第一感觉就不那么好说了。
土是真的土了点儿。但我视听感官的取舍和别人不是太一样。在我映像的取景框里,存留住的是她灿烂明亮的部分。
要说也难怪。毕竟这是楼高街宽,今是而明非的城里。正宗的城里人是看惯了钢筋水泥打造的低沉阴冷的城市表情。习惯了人和人之间恪守距离,相互提防的处世之道。冷不丁一张热脸在你面前打开,不异于在你墨守成规、有条不紊的生活中添了一点儿小乱。这让时时刻刻提防着人同时也被人提防的城里人有点儿无所适从。你莫名其妙也好,从容应对也好,厌恶躲闪也好,表情之后你毫发无损泰然自若的走了,可表情之间,打从你心里脑里抖露出来的本质本性的沉淀物,却不小心滩了一地,无从收起带走。
我看见有人把嘴或眼张成一个诺大的“0”字,表情夸张的卡在那里,能擅长有夸张表情的人,多半精力充沛能量过剩,等他们嘴里咿咿呀呀变换着口型反应过来之后,就会对胖女人报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热情,他们习惯性的用一连串的叠字,肯定自己仿佛心虚的问题,嗯——对对对,啊——是是是,嗳——好好好。脸上笑得也很卖力,笑纹一圈圈的深刻在皮肉里,而笑声却浅浅的浮在汗毛上。
有的人,是对热情和真诚都嗤之以鼻的。看到有陌生人和自己熟人一样的打招呼,很感觉麻烦上身。嘴里有气没气含糊支吾的同时,早动用了一种试图制止的不友好眼神,隐匿的射过去,无声的暗示对方:少来套近乎,少来恶心我。紧接着就是在心里,或对着身边正好有的人小声嘀咕,神经病!以此来证明,这等人和我真的不沾边。
胖女人以宽展的笑脸照单全收。她锲而不舍的招呼着从她身边擦过的她的同类。象一个手持特使令的测试官。一拨一拨的行路人,纷纷前来应试。
对于这样一道来城里淘金的山里人,将会遭遇怎样的礼待的测试题,大多数的城里人给出了基本一致的应试结果。嘴里微笑或不微笑,神情淡漠或不淡漠,在恰当的时候,点头致意,视若无睹的走过。不紧不慢,不骄不亢,优雅大方,敬而远之。无疑这样的礼应是最讲究的。简简单单一动作,含括了这许多的精粹深意。等于些微颔首间,自己已经狠赚了。很近似城里人的消费理念。所以,怎么打量,这份普遍又经典的答卷,都是得高分的。
可胖女人不知道啊,她略显诧异的表情,送走一路对她来说实属新鲜的风景。她觉得城里人好有趣呀,问着不吱声,光哼哼哈哈或点个头,就像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一样,逮个能搭腔的还真难。
胖女人哪里知道这花花绿绿人头扎堆的城里,原是三步一规矩五步一规则的。她更不知道这些看上去表情好像单一而表象似乎一致的城里人,其实就是困在这石头森林里的兽。而她眼里获取的那点儿信息,不过是兽群们统一而基本的兽性。
在这个以建筑物的几何体分割成块的城池里,人们和那些冰冷的各种材质的墙体相互拥抱取暖,组成粗略或细致的各种体系,界限明晰又不可分离。他们住在档次不一的小区或地段,以单元门户划分,以收入等级划分,以权限利益划分,以穿着面貌划分。分来分去,争来争去,比来比去,每个人所得的一小份被认可空间,就是其一身所要看守的全部。为了这份“看守”和“全部”,他们怎能不设防和自爱,怎能不谨慎和矜持。于是点头致意,这种不紧不慢不卑不亢,欲放还收的礼貌行径,就顺着这城市的宽街狭缝大肆蔓延开来,传染流行起来。让所有经过粗略核算,和自己既得利益不是很靠边的人,一律点头概括。不论是和周遭的人维持关系,还是和邻舍远亲保持距离,这样的礼数都是那么恰如其分屡试不爽,得心应手到令人感激。而到了胖女人这里,一个仅仅照过面,且满身饭腥味的异乡人,习惯所致也好惯性延伸也罢,那都是顶级礼遇了。
我并不喜欢吃臊子面。但我还是在那家被阳光格外关照的臊子面馆坐了下来。它比火柴盒稍微大一点儿。生意却比想象的好许多。胖女人售完票就乐颠颠的亲自给顾客上饭。和表情木讷动作机械的小服务生比,胖女人的服务简直是“活色生香”。因为是带了发自内心的热情,和肢体表达的朴实生动。热气腾腾的臊子面放到你面前时,简简单单一句“小心烫着”,和着脆亮的咯咯咯的笑,让人得到很暖意的烘烤,而一张热气腾腾的大面庞,在离开你的视线之后,还会让人随着热乎乎的面条一起捞起,多么热闹的一个人啊!
但那终究是一个人的热闹。胖女人性情所致的在这个城市里散发自己的热情。在她眼里,每个人都那么重要和可爱,那么叫人放不下,不上去招呼一声就不行。但她这种不讲技巧不谙世故的土方子,根本医不好城里人傲慢冷漠的诟病。也软化不了代表城市人基本素质的,坚硬似铁的礼貌行径。整个冬天,我看到那一张被很纯粹的热情燃烧着的红堂堂的脸,象一面旗帜,被匆忙和冷漠的更多人的脸,漂洗、挫伤,终于退色成一块苍白的旧布子,在冬日肃杀的城市背景中,蘸着那一片幸运的阳光,瑟瑟发抖的在寒风里舞蹈。
感觉是那张不知趣的脸终于歇止了它另类的恶搞。终于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还给了城市一角惯有的僵硬表情,和麻木的安宁。人流匆匆的在交织如网的线路上鱼贯而过,象密不透风的墙,找不到任何试图阻断的念头和缝隙。城市生活继续带着它固有的密度和硬度,虫蚁一样不甘的蠕动。而那一片在我眼里幸运的阳光,也以最无辜的表情坦率承认,来到这里,只是光照现象的自然规律和自我完善,那点儿仅有的感情色彩,完全来自我的臆想。等对面那个大缺口被更大的建筑物填补,它将不再来到这里。
时隔多久,又一次坐在了臊子面馆。这个曾经被我抽象成火柴盒的小面馆,生意还是那么好。“大红头”的好使的火柴已不见。柜台后面,宽面庞的老板娘,动作娴熟表情淡漠见好就收的,对顾客点头致意。俨然一个训练有素的城里人。
她麻利的售完票,就习惯性的和服务生一起周旋在顾客之间。显然,她是经过了某种残忍的蜕变,背上生出的一双灰楚楚的翅膀,扇动着丝丝凉风,淡然的走过每个人的身边。
我几乎没搞清那碗臊子面是谁给我端上来的,大概谁端上来都是一样。为此,我的哀痛的心赶去参加了一个小小的葬礼。
热气腾腾的臊子面还在,那热气腾腾的脸,却已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2012-03-20
-
天澜 2014-03-21 08:01:50
不关门的梵高
我不关门是因为我不能打开窗子。窗子窄小的胸围裹住窗外一截陡峭的楼梯,欲罢不能。楼梯扶手由细钢管粗钢管交替构成,一截主钢管陡斜的俯冲下来,像一把情杀的匕首,在正着窗子胸膛半公分的地方,很有悬念的静止下来。然后一个果敢的垂直转折。剩下的半截楼梯,是一只水泥做的狗,卧在我的窗子下边,狗的爪摸到我的门边边。
关于窗子和楼梯功用协调的问题,房东的倾向是明显的。一间瘦瘦的屋子上的窗,充其量关乎一两个人的情绪问题,楼梯却可以把更多的人送上楼去。而楼上风光无限,那可不是在嘴上说的,都是在钱上说的。
关键是,更多的人上楼梯,我就连窗帘都不能往开拉。初来乍到这个院子,我于外部神秘羞涩,外部于我羞涩神秘,帘子是一定得拉上的。混上一段,时间位移,相互关系转换,我个人的身心感受上升到重要位置,一些庸人自扰的顾虑就可以放下了,这时帘子可酌情开合。随着租龄的增长,我在院里熬成了元老级的房客,这时候,对一个和艺术擦边生活本就不拘小节的人,白天不拉帘子的淑女模样,就成了疏忽间想起都觉得纳闷的“明朝那些事儿”了。
那时候的我是既拉开帘子又不关门的。事实上,座南朝北的房子,采光一定是气血不足的孩子,面色苍白。我洞开我的门,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汲取光阴这个难以描述的东西最具象的部分,它该叫什么我说不好,但我知道在我打开门窗的时候,它就为我所用了。
这样我就可以进入色彩的江湖。色彩拥抱在一起,摔打,撕扯,决战出一个全新的天地。那正是我想要的美好或者真相。那段时间,我喜欢用低沉厚重的颜色去探试鲜明亮泽的客观物象。比如,我用焦灼又润滑的巧克力色去涂釉一枚新鲜的柠檬果,让它在清冷的杯盘环境中,散发高温度炙烤下的日子的难堪气味。我又反之,用鲜丽轻快的色彩去表达夜的黑暗。我跟那些对我的画表现出兴趣和质疑的朋友解释:这在我是寻常的经验。黑幕里游动明亮的蝌蚪的音符,才会使夜显得更黑更深。我几乎是在随意用各种程度躲闪不定的红黄蓝绿来装饰我夜的盛宴。如果你还在我命名为“夜”的画里,逮着了柠檬黄和白色的响亮信号,那也不足为奇,谁叫我在深夜里听到了它们的声音。
作画的时候,即使不关门,四周也是安静的,因为心里安静。好像一场成功的的睡眠,切断噪音,拒绝梦扰。耐心陪着我的只有时间。它总是好脾气的欢迎任何的消耗形式,睡眠还是作画在它算作一回事儿。两片依着门窗量身定做的“光阴”的模样投进来,贴在我房间的墙壁地面或者物件上,被一只手轻轻抽动着走。就那样,在日子具象立体的图纸中,一寸一寸一格一格的,挪走。
在调色板上的颜色变得明亮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个可以从向日葵燃烧的花瓣上摘下来的名字,梵高。我会这样想,梵高画画的时候,应该也是不关门的吧。他那么穷窘潦倒囊中羞涩一如我状,应该也租不起宽敞明亮设施讲究的大画室吧?大敞门窗只为借得天光,享得清风的尴尬,在他也不是什么虚荣心煎烤之下过不去的事儿吧?这样想的时候,心情也变得明朗起来,简直是一不小心有了和大师并肩作画的光耀。
但我似乎是错了。一个心里眼里都住着阳光的人,即使穷困即使尴尬,也必须保证住维持精神鲜活的底线。他不同于我等小辈的是,他不能容忍在阴暗小屋里靠门窗里的一线天光,虚情假意毫无激情的,用想象来描绘包括光影在内的苍白物象。他必须将身体暴露在阳光的炙热中,好在无处可避的炽烤下,让灵感和汗珠一起蒸腾至发梢。因此,他厌倦了巴黎的城市生活,爱上了法国南部阿尔那赤裸裸金灿灿的阳光。也许只有八月阿尔的阳光,才和他心中那片天真炽热的天地,合欢相悦。他说,他饱含深情的说:“想画上半打的《向日葵》来装饰阿尔的画室,让纯净的或调和的铬黄,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上,在各种程度的蓝色底子上,从最淡的维罗内塞的蓝色到最高级的蓝色,闪闪发光; 要给这些画配上最精致的涂成橙黄色的画框,就像哥特式教堂里的彩绘玻璃一样。”不管画室大不大,不管门窗关不关,这样一间画室,从主人的心里和向日葵花瓣上折射出的阳光,都已够穿透每个人的心和眼了。
但我想他还是秉性难改的大开了门窗。不是阔绰的金碧辉煌,但一幅幅金色神话般的向日葵,足以让他洞开门窗来耀人耳目,足以让他作为圣宴来款待朋友。况且,他习惯所致敞着的门窗,让他迎接到了八月阿尔打麦场上干爽的空气和升腾的麦香。
或者他会突然的拎起画架进出他的画室也未尝不可。一个创作情绪总是处于亢奋状态的人,一个绝对不会在进出间认真关门和上锁的人,不关门显然省去了他开门的麻烦。他毫无察觉的彰显着他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的艺术气质,神经质的穿梭于他漏洞百出的落拓生涯。他拎着画具去田间小路,去热火朝天的打麦场,去释放那反复折磨着他的创作激情和灵感。身后,是他用以栖身的,除了画作就是画具,没有任何需要防人和避人之物的,找不到关门理由的住所。
而他确实做到了让阿尔八月的阳光在画面上大放光芒,这些色彩炽热的阳光,像一团永不熄灭愈燃愈旺的火炬,在流芳百世的《向日葵》里,在火光流动的《打麦场》里,一路传递。——“画家像闪烁着熊熊的火焰,是那样艳丽,华美,同时又是和谐,优雅甚至细腻,那富有运动感的和仿佛旋转不停的笔触是那样粗厚有力,色彩的对比也是单纯强烈的。然而,在这种粗厚和单纯中却又充满了智慧和灵气。观者在观看此画时,无不为那激动人心的画面效果而感应,心灵为之震颤,激情也喷薄而出,无不跃跃欲试,共同融入到梵高丰富的主观感情中去。总之,梵高笔下的向日葵不仅仅是植物,而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
因为心里的敬畏,因为真诚的热爱,从来不敢挂一幅《向日葵》在我那间阴暗的斗室里,只怕亵渎了一个绘画者关于“爱”的至高纯粹的诠释。
我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中同时容纳“水”和“火”的人。火,就是那赤亮不含杂质的喷发,是蘸着心液的剧烈抖动。水,就是明澈的静止,不能干扰的纯净,是幼嫩而固执的守候。那个人,总是在以水的方式出发,再以火的方式抵达。水和火的天作之合,苦煞的是一个毫无设防的血肉之躯。
割耳朵后的自画像。一场燃烧之后的惨败现场。灰烬和秃焦试图面对,完整不复存在。手和心的颤抖,伴着鼻腔里的丝丝气息,展示活着的真实状态。他从不打算关起自己,打扫脸上的污垢,遮掩自己的感受。自私的人!不顾及所有爱他的人在顷刻间的心力交瘁,感情崩溃。
在室内温度恒居零下的我的另一间斗室。寒冷的空气将颜料在奔赴画面之前打劫成固体的姿态。
一个朋友来看我,他是知道我窘不甚窘的情境的人。在那个尚用传呼机的年代,我在公用电话的一头回答他的问题:就是那一排房中不关门的那一间。然后我裹着那件使我看上去更加落拓的羽绒衣,迅速朝我的栖身之所跑去。
我得在他的摩托到来之前踢开我的门,好让他在第一时间从那排简单的平房中识别目标。
他是我曾经的同窗,才华横溢的艺术的仰望者,因为吃尽了没钱的苦,而猝然折断了理想的翅膀,却从此在商路上敲开了物质的大门,生计无忧。他再次的来劝降我,到他经营不错的小店里去潦得生活上的适度平衡。他是来救我的。
他要我和他一样,关上一扇门,打开另一扇门。
而这一次,我知道我已无力对抗。
但我无法不对我和我们的行为感到深深的可耻的悲哀。迂回还是彻底丢弃,我们都将无话可说。当我们怀着哀悼的情感,面对我们曾经追着神圣的艺术之光的苦乐岁月,我们将是底气不足的背叛者。
无可逃避,这会是每每碰触到梵高,就必然条件反射的心理。这是圣徒和凡俗的不同。他说:“为了它,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由于它,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可以痴颠,可以透支,可以炽亮燃烧慢性自焚,决不迟疑弯曲俯首平庸。那是怎样高度凝练明净纯粹的精神啊,到老到死都不见蒙尘的童稚鲜幼。
到底是在怎样的精神层面下,在自己用画笔描述过的热烈到有痛苦感觉的打麦场,冲自己开了一枪。让爱他的人们突然间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可以减轻这个世界罪恶的解释。只是可以怀疑式的肯定,这一次,他亲手关起了所有的门。
一道超时代的艺术的火光,本因擦亮最前端的指引的天空,却错掷在了懵糟的“古代”,故以导火线引爆的触目,乍现了错乱刺眼的一生。
“……这个世界给他的感觉太过强烈,他只得消失……”
他注定不属于这个世界。
201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