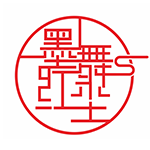阳光照在那些石头上,呈现出让人炫目的质地。如果是白天,你信步走来,就会看到这样的情景。石块大小不一,层层砌筑,被阳光覆盖着,光怪陆离,显得不怎么真实,像是某幅画里的景色一样。
只要看到这个地方,清新的感觉就袭上心头。而漫步其间,一种怅然若失则一次又一次抓住了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总以为它们就是那样的,一直不变,包括这些记忆,包括这些承载记忆的所在,都是安然无忧地存在着的。多年来,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做什么工作,都以为它们始终如一那样存在着。哪怕我一步都不登临,一眼都不去看,它们也好好地在那里,那石头墙,那石头台阶,那石阶两旁石板铺成的斜坡——小孩们滑坡坡,磨破裤子也毫不在乎,照样滑得兴高采烈——,那些散发着强烈的古旧气息的房屋、门窗,那个摆过乒乓球台案的小空院……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它们说没就没了。听别人说起的时候还没怎么太深切的感觉,想再怎么变,也还是那样子吧。直到走到近前,直到脚步再次接触到了那些地面,眼睛再次看到那些熟悉的地方,过去的建筑已然不再,代之以一派新貌的庙宇廊房,才忽然惊醒般,这么陌生,这么奇怪,它们说没就没了。除了少数的石阶,杂呈的乱石,几乎看不到原先的痕迹了。
这些石头台阶应该记得,曾经发生了什么——是谁曾经站在它上面;是谁的气息曾经附着在它上面;是谁的欢声笑语,谁的内心悸动,谁的暗自哭泣,谁的惆怅满怀,在它周遭经久不散,它都知道。没有它不知道的。年幼时候的天真,年少时候的无知,老师们的狡黠,同伴们的顽皮,对异性的心旌摇荡,对世事的懵懂理解……一切都在它的注目之下,在它的记忆里。那群情激奋的赛诗会,那令人心惊的批斗会……激昂的。义愤的。年代的。个体的……都与它相关,都由它见证。它是曾经的见证者,也是永远的见证者。物是人非,沧桑变迁,它不变,那些见证不变。
它本来是座寺庙,是我们侵占了它,利用了它,把它做了学校,做了课堂。从三年级读到七年级,从10岁到16岁,我在这里读了七年书。然后离开,到县城上了高中。它被称作遗山寺,又叫神山古刹,依山就势建筑在定襄神山村东北向的一座土山上,是闻名方圆的定襄古八景之一。它由二郎堂院、上寺、下寺、奶母庙等组成,地势自西往东逐渐高起来。其中,置身于西侧的二郎堂院是一个正方形大院,建有二郎殿三间,坐北朝南,是唐朝形制。殿前建有二郎堂。这个二郎堂院便是后来学校办公室、师生宿舍所在的区域。遥想当年,文人学士纷纷慕名前来观赏遗山景观,吟诗作赋,为后人留下了大量文墨古迹。唐代宋文友,宋代惠勤、米芾,金代孙九鼎、元好问、赵元,元代郝经、郝天挺、赵风,明代安嘉士、王立爱、傅山,清代王时炯、钟一诚、张世禄,等等,数不胜数。尤为著名的是金代大诗人、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元好问,不但年幼时在定襄外祖父家居住,青年时还在神山留月轩读书,经常与大诗人赵元、著名诗人田紫芝等相聚遗山……在战火和文革中,寺庙不幸遭临厄运,二郎堂院的二郎殿被拆除,其余尚保留原建筑。上寺除留下建于清朝乾隆二十三年的魁星砖塔外,其余均被拆光。下寺原建筑已荡然无存。……世事难料,如今,它将再次以寺庙的身份面对世人。目前,二郎堂院已修复竣工,上寺的大殿也已建成。我读书时候作为教室的所在区域楼院则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工程负责人告诉我说,修复建设工程会逐步进行。当然,彻底复原是不可能的,破坏掉的,永远无法还原了,修旧像旧只能是一种初衷,一个愿景。说着话,他的目光里露出一丝无奈,一丝惋惜。我就意识到,神山古刹向寺庙的回归,既有朴素的人文思想,也有佛学层面上的意味。其中内蕴,耐人咀嚼。
我在二郎堂院里踟蹰漫步。阶石确乎是苍老了。剥蚀的痕迹十分明显。坑坑洼洼、粗糙不平的表面,依然亲切,蓄满了往日的时光。二郎堂院东侧的那个小院里,曾经是学校的粪肥堆积处。同学们把各自拾来的粪肥倒在固定的点上,每个班分开倒。有专门的同学站在那儿拿着个本子做统计,谁总共几箩筐了,谁领先了,谁落后了,哪个班第一了。二郎殿后面,曾经是学校的兔棚。每个班的同学轮流割草喂兔子,有的班不会喂,没几天兔子就所剩不多了,就到养兔子养得好的班里取经。
这个院子的西面,原先是有一架葡萄架的。葳蕤繁盛的一长串葡萄架,由西向东延展着,由木头桩子架起来。1974年的那些赤日炎炎的中午,老师们午休了,学生们还没到校,一个少年搬一只小板凳,安静地坐在葡萄架下,一边看书,一边守护那些晶莹剔透的紫色葡萄。总有些淘气孩子,会趁机溜进校门,打这些还没熟透的紫色葡萄的主意。少年佩戴“红哨兵”袖章,捧着小人书《列宁在1918》。少年的眼睛是明亮的。少年长着一副雪白的牙齿。少年的黑头发在少年的脑袋上蓬蓬勃勃地生长。时隔近四十年,我很难想象,曾经的自己竟然能够那样一本正经地独自完成这项校领导指定的任务,日日坚持,未曾懈怠,要多像回事有多像回事。这个11岁少年曾经的行为,如今的孩子看起来,或许无法理解,似乎十分的幼稚可笑,可那时侯就是那样,年代的特定因素界定了你,裹挟了你,左右了你,你置身其中,只能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般,顺其自然。这是葡萄架下的一串绿色故事。这个影像定格在时光的记忆里,定格在我的心里,历久弥新。遥想当年的同时,我的心底升腾起一种十分纯洁的感觉,就像曾经坐在葡萄架下静静地看书时所拥有的感觉一样。
一进校门,左手坐北向南的,是几间小房子。正是通过这些作为校图书室的小房子,我源源不断地阅读了大量长篇小说,从而奠定了自己对文学最初的热爱与自觉追求。
那时候我是独自走在宿舍外面,许多念头在我脑袋里冲来撞去。无法形容的情绪鼓捣着我年少的心。我在校园里徘徊。老师们在办公室打扑克,高声的叫,大声的笑,还拍腿,拍桌子。没人理会到我。我孤零零一个人。12岁的少年独自在校园里彳亍。时间走过去。只有瓦蓝的天幕上,星星望着我,眨着眼睛。没有月亮。
然后就热闹起来。没几年,子弟兵纷纷来到了,这个老师的儿子,那个老师的闺女,另外几个老师的妹妹,大大小小有十几个……大家没过几天就熟惯了,热热络络地说话,彼此开着玩笑。吃饭时候,位于二郎堂院西南向的伙房里简直闹翻了天。是从什么时候起,我这个孤僻的人,也融入了这个阵营。每天晚饭后,老师们去上办公,我们子弟兵齐齐聚到伙房,做饭的老王是个会说笑话的人,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说着闲话,要不就轮流讲故事。轮到我,我就讲《大刀记》,讲“瓦尔特”,讲得大家听直了眼。那是我有限的开心时刻。哪怕我忘记了,张冠李戴,七丢八拉,也没关系,可以忽略,可以后补,一切随心,听得就是个乐呵。都安安静静的,大家的眼睛那么明亮。老王吧嗒吧嗒抽着自卷的小兰花,也听得入神。随机应变是种本能。要想讲好故事,我必须随机应变;要想融入他们,我必须随机应变。置身当时当地的情境中我毫无觉察,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现在隔了三十多年,我隔空相望,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仍然无法说清楚。

 【红尘有你】在时光的那一头
【红尘有你】在时光的那一头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