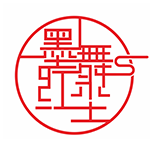一、从死亡的必然中了悟人生
“关于死亡的教育/我们从认识蚂蚁时就开始了/蝴蝶、小鸟和牛羊,都给我们上过死亡课/后来是祖母外祖母,祖父外祖父们/他们的演示,比课堂上老师的讲解更透彻……”(《死亡教育》)。这是一种近乎残忍的“教育”——只给你结局,不给你道理;只给你伤口,不给你药物。身边生灵的消失、亲人的离去,特别是姐姐和哥哥的早逝,无异于一次次劫难,在川美心中留下抹不去的烙印,让她逐步体悟到了生命的苦与短、小与轻。是啊,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演化史比作24小时,属于人类的则只有半分钟,而这半分钟里曾经出现过多少茬生命,我们不得而知。原来,我们平时所认为的一切重要的东西,在浩瀚的宇宙里是多么微不足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正是由于继承了古人这种生死观,洞察了生命的单向性,川美才会终于意识到:“天地间,那么多死,给你看/那么多告诫和劝慰/让你接受死亡这回事/——‘不是应该,是必须!’/——‘不是不甘,是安心!’”(《死亡教育》)。从“必须”到“安心”,中间经历的不仅仅是时间,更是炼狱般的心灵磨砺与自我调治。“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也许正是对于川美“安心”的最好诠释。
风吹我之前,吹过什么?/山丘,树木,树上的小鸟/白发人吹弯了腰,状如飞蓬//风吹我之前,吹过许多朝代/皇帝和皇后也给吹跑了/风,依旧吹,吹着野草和臣民……//风吹我之后,还吹什么?/山丘、树木、树上的小鸟。白发人状如飞蓬/风无死,可作弄万物(《风吹我》)
风本身就是一种变化莫测之物,用来描摹变幻莫测的尘世再合适不过,但能把“风吹”这么一件小事写得如此开阔宏大、寓意深远的委实不多。从古到今、从皇帝到臣民、从动物到植物……川美以一个思想者的身份,带着我们随风而动,通过一幅幅立体可感的图画,让我们看清了生死与轮回、沧桑与虚无。当然,我想说的并不是这种沧桑感、虚无感,而是川美在叙述过程中始终保持的那份淡定与从容。不难理解,面对那些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事物,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弱女子)除了自言自语式的追问,没有慌乱,没有“怆然而涕下”的感伤,他(她)的境界与格局必定是超乎寻常的。不然,也不会诞生结尾“风无死,可作弄万物”的点睛之笔。
辛波斯卡在一首诗中写道:“同样的事不会发生两次/因此,很遗憾的/我们未经演练便出生/也将无机会排练死亡。”但这种“排练”川美却做到了。她一边思考“怎样的死相是好的”,一边想象自己的《以后……》:“只为你一人到来的末日/死神温柔地抱住你,吻你的嘴唇/喂你拌蜂蜜的白色曼陀罗花瓣……”在这里,“末日”是庄严神圣的,“死神”是温柔体贴的,“死亡”的现场是充满了人情味的。更有意思的是,她竟然要自己的爱人“练习一个人上床”,以适应总有一天会降临的“一个人的生活”。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只有对生命有着深刻了悟的人才有能力建立。当然,这种“练习”并非只为“最后轻松地”“背走”那只死亡的“黑包裹”,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在为自己的灵魂寻找一个安放的空间。她的另一首《我有野心,自称灵魂》,寓意非常明显:
六月了,多么快/而未来的七月,或八月/乃至九月,之后,更多的九月/你不在故乡,也不在异乡/雨季到来,枯萎的梦一夜复活/疯长在撂荒的土地上/我却多么喜欢辽阔的荒野/荒野中,那自在的野花、野草、野牛、野马啊!/我有野心,自称灵魂/在你们当中,在大地上游荡
“你不在故乡,也不在异乡”,在哪儿?答案是“辽阔的旷野”。这“旷野”,可以理解为狭义的、真实的旷野,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精神意义上的空间——那是灵魂居住的地方。这里的“野”,可以理解为“野外”的“野”,但我更愿认为是一种不受任何羁绊的“自由”,因为这样才能配得上“自称灵魂”的“野心”。说到自由的灵魂,忽然想到川美的另一首诗:“园林里,一棵文老虎的榆树/活得痛苦,它正一点一点死去/它死去,好把老虎放出来”(《那些树》)。这里的“老虎”是灵魂的代名词,它渴望长啸山林、奔驰原野,而今却被“囚”在了一棵“榆树”上,“榆树”不死,“老虎”就永远冲不出“牢笼”。我不知道这是否代表了川美曾经的一种情绪状态,但可以认定,这两首诗从不同角度映照出了川美对“灵魂自由”的期待与呼唤。
二、从虚幻的镜像中撷取唯美
如果对于生命的观察只停留在“了悟”层面,那么这种诗写是无效的,起码难以形成更具引领价值的文本。在集中阅读川美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坚信这一点。可以说,川美的诗歌已经离开“教化”的功能模式,随着灵魂抵达了一种“神性”的美学高度。关于“神性写作”,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公认的概念,也注定不会成为当今诗歌的主流,但把它当作一种促使自己产生敬畏、得到净化的写作理念,应该不会受到过分诟病。
……那又怎样?如果我确知/死神在前面的路上等我/我会一路走一路为它采撷小野花//我等待,而深谙等待的美学/万物都在躬身行进/我却成为时间之畔的静物……(《等待》)
在一个采访中川美坦言,她喜欢艾米丽•狄金森、辛波斯卡和玛丽•奥利弗,因为“她们都是安静低调的诗人,在这一点上,我自认和她们是一类。”艾米丽•狄金森被公认为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女诗人”,她的死亡诗赏心悦目、独树一帜,在打破传统诗歌禁忌的同时,为读者找到了另类精神出口。一向与世无争的川美显然乐于接受这种影响,并自觉付诸创作实践。在川美眼里,“死亡是这般可爱的一次旅行”,不但不让人产生畏惧,反而令人身心愉悦、自由舒展。上面这首《等待》,无疑来自《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的启示,但川美并未走狄金森展示某种“过程”的路子,而是强调了一种源于灵魂的“静”。这种静,似秋后的原野、月下的流水,又似微风中的兰草,空澄高洁且带有一丝孤傲绝美之气,与英国浪漫主义中的“神性自然”息息相通,成为川美诗歌品质坚实的组成要素。“她的诗歌中有一种神灵,让万物附上了灵性,让人充满敬畏。仿佛她能通晓自然和万物的心,冥冥中能听懂并感受到隐藏在树木河流以及花草鱼虫中的秘语和真意。”评论家李犁先生如是说。再看《拆钟人》:
……拆钟人不相信时间也会死/他找来组合式螺丝刀/迅速揭开钟的后盖/像撬开一口棺材//拆钟人惊讶地发现/时间已腐烂成一具枯骨/牙齿咬着牙齿,十分可怖/看不出原先是狮子,还是老虎//拆钟人继续拆钟/把卸下来的骨头装进蛇皮袋/并最终埋在一棵桃树下/他低头干活,桃花落了一肩膀
川美一直在尝试一种用诗意“触摸时间、试探时间的方式”,寻找一把“用诗歌撬开时间的密室”的钥匙——因为时间是生命的载体,也是死亡的温床。作为时间的计量工具,钟表无疑具有先天表达优势。时间会死吗?会死而复生吗?拆钟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埋葬时间的背影在“桃花”的衬托下显得那么美、那么孤独。“死亡是花,只开放一次”(策兰语),桃花,比其他花朵更绚烂、更妖艳,更能点破死亡的“迷人”之处。而这里的“埋葬”,其实是一种“种植”,为人类留下了希望和寄托。身为另一个“拆钟人”,川美用她的文字拆解了我们的目光,却重组了我们的想象与情感。

 一切可触摸的都将逝去
一切可触摸的都将逝去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