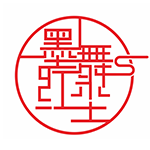但有时竖著耳朵,也是什么都听不到。等到反应过来,西面已经拉开一片火焰。恶行是黑暗中的阴影,神出鬼没。以往我对顺风漂来的汗味、腐败味、腥臭味都十分警惕,但忽略了其它的气味。看不见的时候,你就会懂得,不同的人散发著不同的气味。小刘在这里时,身体上就散发著一股垃圾桶里的味道。他从不洗澡,还爱躺在废品堆里晒太阳。可一旦在站里呆久了,你就习惯了他的这股味。小刘去种草莓,脸变黑了,皮肤粗糙,身体却换成一股微酸的草味。我知道自己是什么味道。一旦失火,皮肤上还会沾著烟火与潮湿的气息。滚远点,你就像条烤过的咸鱼!老板那时就这么说。然后,我就提著桶,去水池边冲洗身体。
阳光很好的天,我就往纸板上泼水,不仅防火,还可以增加重量。所以老板看见了也不会说。他笑眯眯地抽著烟,一边转悠,一边告诉其他人,说还是哑巴有头脑。有时,老板会给我一瓶喝剩的酒。在夜里,喝著酒,我能想很多事,等天亮了,像一阵风吹过,又什么都忘记了。我看见一棵树,它也在摇头。有时,在下午醒来,遍地白光刺眼,让我很生气。我想要抓住那个放火的人,用木棒狠劲揍他。
我感觉自己在追随著夜的脚步,不停地转悠。拄著棒子看星星,侧著耳朵听动静。我看天空的时候,月亮如钩,冷得发白,像要滴出水来。空荡荡的窄巷很长,尽头有一盏灯,在地面上晕黄出一大摊来。老鼠穿过光跑了,贴地的纸片跟在后面翻动。也许是因為宁静如此,人们才在夜晚做梦。梦见些乱七八糟的事。我用思想来代替做梦,想些乱七八糟的事。例如,逃去去乡下,帮人种菜,或者像小鱼一样,四处求乞,当然,还要找个女人。夜晚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不过放火的事情更让我闹心,只有暂时放下心事,先抓住他。这么想著,我已经走到路灯下面,再往回走,爬上那堆废铁,坐下。凝视著断墙处,鼻腔里一大股铁锈味。我突然想到,这低著头的姿势,像小鱼,一个算命师。屁股下面冰凉,我得想点好事,让感觉好受一些。当老板让我把被褥搬进来,还可以将房子粉刷一下时,他还说好好干,什么都会有的,女人也会有。所以我得坚持,直到老板笑起来。我就这样守了九天。从外面看,你一定以為站里没人。
坐著黑夜里,心会慢慢静下来,也看不到周围的肮脏不堪。风若有如无,银河闪闪发亮,让我感觉做人的黯淡与寒碜。天亮以后我就睡觉,然后中午起来,该吃吃,该喝喝。天黑了,提个棒子绕墙便走,敲几下破铁盆。待四下杳声息,回到铁架上坐著。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梦想是有的,给谁讲呢?不著急。以前会说话那会,还小,一门心思就想早点长大,仿佛有无数大事等在很多年后。然后有一天,突然就哑了,独自性急如焚。每天熬苦药喝,睡前再加喝一勺蜂蜜。请人在头颅上扎银针,颤悠悠,像个刺猬。或者去城里的大医院,在门诊张嘴伸舌头,进暗室照光拍片。医院、药片、针水、车票花费无度,父母说,已经把以后读大学、娶媳妇的钱都用光了。再医下去,人死抬埋的钱都能全部用尽,回去吧,看不下去了。起先是自己不乐意,在医院外发疯,碰到什么都拳打脚踢,后来手破了,脚肿了,就流著泪回来了。把自己关在屋里住了一年,才出来见人。父亲抚摩了一下我的头,没有说话。又听说有这么一个偏方,每天清早起来后,去找一口井,然后对著下面呵气,连做七七四十九天,最后要喷出的是一口黑气,准好。母亲说,就像癞蛤蟆吐气,这不大好吧。我试了一次,天亮趴在井沿上,呵气如雾。猛抬头,看见太阳从山顶上哗啦啦冒出来。同时,听到身后还有人喊叫起来,吓我一跳,以后就再也没做过了。
要么是心诚则灵,要么踩了狗屎一脚,我无法相信捉住的会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不是连续守了九夜,我也就远远地敲一下盆算了;但老板的脾气让我嗓子发干,寒气贴著屁股透进来,在肚子里纠结成团,我不在乎对谁挥去木棒了。那是子夜时分,虫子都叫累了。尽管巷子尽头灯光很弱,我还是瞅见了那道慢慢移动过来的影子。我憋足了气,也悄悄走下铁架,靠近矮墙缺口。我本来想只要他跨进来,就一棒子砸过去。可他不慌不忙,走进来,在蹲下来前还先提了提裤腿,好像怕弄皱了裤缝一样。我只得弄出点声音来,示意他跟我走。当时,我还有点心慌,但他一点也不著急,跟著就进了屋子。在灯下,看他那一身打扮,只适合在临河街的商场里进出,大把地使钱,购物。他不坐,就站在那里,略微发福,衣装笔挺。我比划著问他為什么来放火,但他一言不发。还摸出一包烟来,抽一支递给我。我不抽烟,但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这样一支烟的价钱,够我吃一顿饭。每当看到他嘴边喷出的烟雾时,我都极力忍著不举起木棒,可却始终无力比划出让他滚蛋的手势。有一种人,好像做什么都理直气壮,你不可能赢他。在街上,有人就爱掐瞎子,骂哑巴,踢瘸子,扒小朋友的裤衩。已经麻木了。他掏出一张钱扔在床上,丢下烟头,向外走去。风从门外吹进来,吊在电线上的灯泡晃悠个不停。
有天下午,我在环城路上闲逛,遇到了小刘。他刚从一道大门里走出来,双手都是油污。“我做修理工了。”他说。我点头,但他还是晃著两只手。我突然想起他不在乡下种草莓去了么。我们在路边坐下来,他捡片叶子,擦著手上的油。“草莓不好买,种的人多了,”他说,“乡下没意思,就剩下些老人和孩子。赚钱不容易啊。想想,还是一个人过会好一点。一人吃饱,了无牵挂,谁都可以的。我媳妇是个好人,肯干活,也爱热闹。可是乡下太偏僻。实在没办法。”他盯著我,我在摇头。他把叶子踩在脚下,直到碾碎,而我则在想他说的“一人吃饱,了无牵挂”。小刘知道我没弄明白,他吐了一口唾沫。“我离婚了。”他说,“不然又能怎么样呢?”
我也跟著吐了一口唾沫,把道路上的尘土和汽车尾气吐出去。整个下午一片苍凉,分不清是阳光的颜色,还是尘土的颜色。我一直走到天黑才回到收购站,躺著屋子里,闻著飘进来酸腐气息就睡著了。第二天清早,我从床下翻出那张钱来,去买回两瓶酒,一饮而尽。人好像飘在水面上,心跳到喉咙。最后,吐口水,都是苦的。
我萎靡了好几天,乱七八糟地冒著一些念头。有的念头一闪而过,含义古怪而不安;有的念头被拉得很长,慢吞吞经过著,和蜗牛爬过玻璃一模一样。我不想这样鬼迷心窍。為了消磨时间,我将小刘的离婚比划著告诉了老板。老板娶过三个老婆,一定能说出点道理。他顿了顿,吐了一口浓痰,说,别傻了,没有钱,谁有工夫操这份心。他让我去把废轮胎垒起来。我干得汗流浃背时,听见他走到身后,先点上支烟抽著,又弯下腰拂去裤脚上沾著的碎屑,说:“这事不新鲜,都什么年代了。”所有的人都爱拿年代说事,不知这是自信,还是愚蠢。
我又在临河街上遇到了那个人。他刚下车,自信满满,像个电视里的主持人。他目光从我脸上扫过,然后顿住。我面朝他蹲下,在地上画个圈,然后吐唾沫。他也许没看明白。这是我最狠的一招。几天后,我无意中翻到一张旧报纸,报道说,某日清晨7时许,某花苑小区一户人家发生火灾,房间里的一家三口均被烧死,其中一名死者是儿童。经有关部门初步调查认定,事故原因是屋中人纵火自杀,儿童则很可能惨死于父母的纵火之下。而据知情者透露,死亡的屋主平时就有纵火倾向,原因与抑郁有关。我不禁联想到那个人,想到他衣冠楚楚的模样。火焰确实像野马飞驰,能吞噬现实,释放内心的禁锢。但我还得加倍小心,打起精神来,每夜绕墙疾走不歇。木棒敲打破铁盆,怪念头总是带来恐惧。
雨季到来,可以整夜呆在屋里,但谈不上有什么可高兴的。雨滴敲打著屋顶,孤独,人却静不下来。声音照样像潮水一样无休无止,湿淋淋地贴在皮肤上。门外的地上冒出些草木。其中一种,叶片细碎,黄昏时才开花,花朵如淡红色的瓷杯。到第二天早上再看,花瓣已经收束,呈白色。花开得纳闷,好像不想让人尽看。有时,小刘会来。他不管我是站著,还是出去,又转回来,都只坐在床上,说话。他对我说,我只需要听著,不需要点头,也不需要摇头。听著就好。但不许让别的人知道。

 哑巴说
哑巴说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