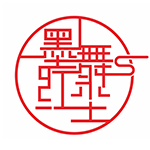他所组成的向黑暗开战的队伍,也是有这些“小屁孩”组成的。问题的关键是,即使退一万步讲,他的这场战争即使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并建立了自己的“新天国”,那么“新天国”一定是一个充满道德、正义、公理、良知的“新天国”吗?不然到了今天为什么共产主义仍然是传说中的“乌托邦”?远离了神性观照下的人本主义的极度膨胀的无助的绝望的战斗只会摧毁神性,而不可能建构神性,只能使希望更增添了一份绝望。宁芩不会不明白,这场喧哗与骚动,只能是痴人说梦。
当战斗最终以失败告终,当狂人被绑到了电椅上,随着“女妖精”按住了电钮,“什么也不知道”的狂人的希望成了最后的绝望。
所谓拯救,并不是祈求一个来世的天国,而是怀着深挚的爱心在世界中受苦受难!
第二章:《神鹰》、《失落的春天》——神性的幻灭
冬夜,沉沉漆黑,深沉的夜的黑暗,无边无际。
案上的灯,照亮房间的一角,照亮不了我的心。
——宁芩《在灵魂的深深处》
继十九世纪的尼采喊出来“上帝死了”以后,二十世纪的福柯又宣布“人死了”,于是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审美主义泛滥于世,造成人类精神的空前混乱与恐慌。然而仍有不少思想家和哲学家认为,只有当思想和生命与某种神圣的东西连在一起时,人本主义才有基础,如果人本主义听其无神论的虚无主义推至逻辑的极端,它必将以自我毁灭而告终。
由于对超验神性的构建的缺陷与不足,由于爱和信仰之维的缺乏,《狂人笔记》式的写法似乎走向了一条死胡同,这时宁芩转而探寻人性中最接近于神的那一部分,写出了像《神鹰》和《幻灭的春天》这两部力作。然而这种放弃超验,而从经验和先验的对神性探索的方式,最终导致了神性的彻底幻灭。
《神鹰》更像一则寓言和童话故事,或者如燕卜荪所言的“牧歌”模式。用一个简单得多的世界来映照一个远为复杂的世界,特别是深谙世故的读者的世界。这样的(有普遍意义的)人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它是一个表现带有普遍性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在表现时既可以有新鲜的洞察力,也可以与问题保持适当地美学距离。
《神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小山村。小说中的主人公苏西是一个勤劳勇敢的少年:
他的头发如丝绸般光亮柔软,眼睛如黑夜里的明星,脸庞如白玉雕琢,他对人礼貌又乐于助人,村里的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不喜欢他。⑩
可突然有一天他变成了一只雄鹰,当他飞回村庄与亲人们相认并团聚的时候,却遭到了村民们的集体攻击,他们要杀死他。绝望的苏西面对村民的攻击,既不能申辩,也不能以恶制恶,最后只能选择撞崖而死。
《神鹰》具有着丰富“潜文本”,它在不同审美视角与情感状态的观照与体悟下具有多重的审美意蕴,这同时也证明了它是一篇杰出的艺术作品。在《神鹰》中有着多重对人性的隐喻。苏西在没有变成鹰前,是一个受人喜欢的好青年;当他变成鹰后,却成了人人追打的对象。同样是一个“苏西”,只是呈现或者存在的方式不一样,却受到不一样对待。它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身份等加在人身上的一切附属物只是一个符号,甚至人本身也是一种符号,对个人来说,他人永远是高墙或者地狱。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永远是隔膜,而难以沟通。这就触及到人的生存状态及人的基本关系这个形而上的人本命题。此外,它还触及到人的基本根性的问题。在《神鹰》中,人性是自私的,集体攻击变成鹰后苏西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苏西的鸣叫是一种不祥的预感或者担心鹰会首先攻击他们。人天生就具有自我保护性并有自我保护性的使然而具有攻击他者性。同时人性又是愚昧无知的,贪婪的。村民们轻而易举地就相信巫婆出于利己之心的蛊惑,这里并不排除村民们和巫婆一样垂涎着苏西身上好看的洁白的羽毛。
也许在作者宁芩看来,人的本质是恶的,诸如“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话语只是一句骗人的教条。人本身是缺少神性的,想在人性中嗅到神性的芳香,只会导致虚空与绝望,只会导致对美好人性的失望,对人性中是否存在神性这一命题的幻灭。
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就是小说发生的故事环境背景:
在湘贵川之间,雪峰山高耸入云,山下,有一个小小村落,村里的房屋全是木头搭建,门前的院子用树篱与大路隔开,树篱上爬满了各种青藤,开着牵牛花、黄丝花,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院子里有一畦一畦的菜地,种着萝卜、卷心菜、莴苣、青瓜、苦瓜;门前栽培着一株株大山深处特有的佩兰芝草,这些花草四季都开放,芳香四溢,沁人心脾。两边的空地上,有冬瓜、南瓜、蓬豆,有的已经爬到了屋顶。屋顶上爬满了各色的青藤,也缀满着各色的花朵,远远的看去,像一座青翠苍绿的的开满野花的小山包。蜜蜂一天到晚在树篱里嗡嗡地飞来钻去,不知疲倦地为山村纯朴辛勤的人们唱着欢快的赞歌。屋后的院子里,猪在圈子哼唷着,羽毛鲜艳的大公鸡威武地追逐着一群咯咯咯叫个不停的母鸡,不时昂头高歌,喔喔喔!
小山村美丽而宁静,村中,有一条清澈的山溪,从高高的山上一路欢歌而下,在村头日夜推动着古老的磨盘,然后,又灌溉着村子下面的稻田和菜地。⑪
这无疑是一个“世外桃源”,一篇“竹林的故事”,一座“边城”,天然、纯净、原始、朴拙,是孕育人性善与美的温床。废名会在这里找寻禅宗之趣以及天人合一的超脱之境;沈从文会立足此地耐心的建一座希腊的小庙,里面供奉美好的人性;后来的汪曾祺则会不厌其烦絮叨美与和谐。然而宁芩却是残酷的,他在别有用心(自觉地)铺述优美的宁静的自然风光后,直陈疯狂的暴力的血腥的场面。这种强烈的反差,无疑是对人性美和人性美制造者的巨大反讽。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尚且如此,那么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又将如何?《狂人笔记》后的宁芩仍是那种绝望的幻灭心态!
而这种绝望感和幻灭感到了《《幻灭的春天》这里,不是逐步消淡,而是愈演愈烈!
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幻灭的春天》,成功的可喜的为当代中国文学画廊塑造和增添了多余人的角色。《幻灭的春天》可以说就是唯特的故事,他的个人命运是整篇小说的主要情节。在这部小说中,宁芩通过对唯特这个人物及其命运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处境。有了这些依据,我们姑妄称唯特这个“多余人”是病态社会和人生困境的现代人的典型。这个典型可以和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一些经典形象差可比拟。比如围城中的方鸿渐,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比加林。如果把他放进20世纪世界的文学坐标内,就其表现出的现代性方面,又和卡夫卡笔下的那个既无望进入城堡又不能离去的无名人,乔伊斯笔下反英雄,普鲁斯特笔下追忆者,迷惘一代思潮中的迷惘者,存在主义文学中的恶心者和局外人,新小说中的走向死亡的人,黑色幽默派笔下的那些面对社会权威而无能为力者以及索尔.贝娄笔下挂起来的人等有着惊人相似性。可以说他们是同病相怜的病友,是现代人的不同变体,他们不约而同地折射出人类的永恒困惑和人生的永恒困境,体现出作者们对人类的基本存在状况和人的基本关系的深刻思考。只不过与这些经典形象比较起来,唯特这个形象在特殊性上稍强,在概括性和普遍性上稍弱。举一个列子,比如在《围城》中,由于作者钱钟书并未有赋予方鸿渐的人生追求以任何可以称之为崇高的理想对象,亦无任何堪称伟大的价值目标,而只是具体生动地展现了最起码,世所公认的几种人生价值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例行过称———一个失败和失落的过程,从而使得方鸿渐这样一个形象普通的现代人之极为平凡的生命历程具有了极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意义,他的某些人生经验﹑生存困境,以至于心灵的困惑,是现代人的普遍遭遇和共同感受。而唯特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现象,很难把他归入普通人的范畴。他身上兼有诗人的激情和哲学家的思考,并怀有以己之才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但是他对社会是拒绝的,因为清高与自洁而拒绝融入,他的遭遇只是一类人的遭遇,不具备强大的概括力和统摄力。

 从神性到兽性
从神性到兽性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