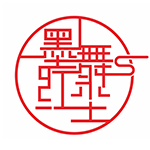鉴于此论不是本篇所论述的重点,此处不再作一一展开。
笔者认为,在《幻灭的春天》中,宁芩旨在探寻爱情的神性。在小说中他借主人公唯特之口,说出了这一主旨: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去找回前世的爱人,死心塌地去爱她,把前生未了的遗憾完成,把理想臻于完美。
生生死死,来来回回,活在这个人世间,爱是才是唯一的意义。⑫
的确,在小说中,无论是唯特还是白小玲都是为爱生、为爱死的角色。白小玲疯狂地爱着唯特,这种爱,没有理由,不附加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私心,毫无保留的,甚至不惜奉上宝贵的贞操和灵魂,原因只是因为一个前世的“白鹿”和“僧人”的故事。宁芩把白小玲的爱情置于一种神话的模式上,最大限度地考量一个女人在爱情中的勇敢,执着,牺牲,奉献和担当。按照世俗的看法,白小玲和唯特的爱情本身就不存在对等性。“白小玲是个好女孩,她美丽、温柔、聪明、善良、活泼,认识她的人都夸她,追求她的人很多”,而且她出生在一个副市长家庭。而唯特身份只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一个办公室的小职员,而且敏感,偏执甚至有点神经质,这无疑是一个““白富美”和“屌丝男”的故事。然而这个“屌丝男”偏偏对“白富美”不感兴趣,唯特爱着虚幻,爱着一个影子。他的爱情是一场精神上的恋爱,它包含着自恋。他爱的对象到底是谁?他自己也无法回答出。只是到了乡下才猛然觉悟出自己多少年爱的人等待人竟然是儿时的玩伴———莺莺。然而这里有多少爱的成分?它其实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文化基因在文人血液中的心理传承,或者说是一个儿时的天真的承诺。唯特是一个审美主义的“柏拉图”和“贾宝玉”,以自由之身为借口,拒绝生产,拒绝担当组成家庭后的责任与义务。
当他和白小玲发生肉体关系后,小说这样写道:
我的心在流血。
我的一生将在沉闷、单调、平庸、琐屑之中和这个女人度过,没有一点激情,生命如同被封埋在千年的地下,吹不进一点新鲜的空气,分辨不清白天与黑夜,分不清昨天、今天和明天……
“没有了希望,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在心里痛苦地呼喊着。⑫
当白小玲绘声绘色地为他描述以后家庭的蓝图时,小说又写道:
我仿佛真的看到了,看到了和白小玲厮守在一起的日子,还有那又美丽又温馨的“爱的小屋”,看到了以后的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麻木沉闷的时间长廊,没有激情,没有灵感,所有的日子,全长着一副苍白冰冷的脸孔,难道这就是我和她的爱?这就是我爱的归宿?
不!这分明是我人生的囚牢,是禁锢我灵魂的枷锁,是我的理想和自由的绞索,我想要呐喊,要挣扎!
我肉体逃不了了,但是,我的灵魂早就逃走了。
我的灵魂啊,你逃到哪里去了?我怎么找寻不到你的一丝踪迹?⑬
在这里唯特完全忽视了一个女人为自己“献身”勇气与真诚,而是认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绑架。发生关系即意味着要结婚,结婚就意味着走入围城,走进坟墓,这种对自由之身的高度看中,是文人们最大的劣根性。
然而就是这种道德约束也失去了效应,当唯特发现了梦中的情人莺莺后,并从保罗口中得知莺莺目前的状况和处境,唯特毅然决定抛弃白小玲,并要求她打掉腹中的胎儿,从而使自己了无牵挂地去拯救自己的梦中的情人莺莺。苦苦哀求的白小玲,在求告不成情况下,绝望地选择自杀。
白小玲并没有死去,经过抢救她活了下来,但是“因为脑缺血留下了后遗症,模样变成傻呼呼的了”。唯特因此受到了良心的强烈谴责,决定用婚姻来给自己赎罪。可是当他得知莺莺的最终情况后,彻底绝望了爱情,幻灭了存在的意义,自杀了。
在这里我们无需责备唯特的不负责任和缺乏担当——他彻底抛弃了因他而憨傻的白小玲,让白小玲一个孤独无助地面对以后的生活,也无需批评他的懦弱与逃避,对一个审美主义者来说,当生命再也没有美,当爱情已缺少了神性的价值存在,活着也就是行尸走肉,与死无异。
当世俗的爱情面对神性的爱情,灵与肉无法统一且难以调和,当进行了一切追逐与探寻之后,证明神性仍是空中楼阁遥不可及,宁芩的绝望感幻灭感日趋加重。他在《在灵魂的深深处》中痛苦地绝望地写道:
时时仰望天空,没有佛光,没有上帝。
身体的一阵颤栗,牵扯到了灵魂。
第三章:从《发现华南虎》到《魍魉村庄》——兽性的堕落
一只可怜的家禽,它至死也不会明白
主人豢养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一天到晚快乐地觅食和交配
它爱惜自己的羽毛使它明亮鲜艳
它甚至于异想天开地想要替代黄牛为主人去犁田
可是,主人只想在它的肉体丰腴之后摆成丰宴
———宁芩《等候光的时候》
上帝的超验世界消失以后,便剩下个体生命的绝对性,“此”被推到了首要地位。既然唯有生命值得肯定,那么在审美的光照下,所有的生命本身所连带的丑恶、纵情、浑浊都得到肯定。再也没有神性的眼睛盯视生命本身没有洗涤的原始性,它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徜徉于市。正如荣格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指出的一样,“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美学的水平了——丑也是美,即便是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惑人的审美中发出诱人的光芒”。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推理出这样的结论:绝望了神性、放弃了超验思索的宁芩在创作倾向上会自然而言关注肉体生命本身,因为他的世界观里已经种下价值虚无的种子。既然一切价值都是虚无缥缈的,那么不虚无缥缈的也只有肉体生命本身了。这和那些新写实小说家们在放弃了理想、英雄、神圣与崇高之后,只能坠入俗利、现世与虚无是同一个道理。新写实主义者认为生活就是世俗,宁芩则认为,生命就是欲望,特别是肉欲。他们犯着同样的毛病——偏至。认知的偏执和美学把握上的偏至。
在《欲望人类》中,宁芩这样写道:
且将人生比作一只风轮,绚丽多彩的风叶不断地转动着,绽放出炫目的美丽,驱使生命的风轮转动的动力是欲望、各种各样的欲望。
在形形色色的众多欲望之中,有一种欲望,它是最根本最原始的,它是各种欲望之母,它派生出各种其它的欲望,如金钱、地位、名誉、好吃、贪婪等等,这就是性的欲望。
从纯生物的角度来观察,饥渴求饱的欲望、寒冷求暖的欲望、疲乏求安的欲望、升官的欲望、发财的欲望……其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好营养好自己的个体,为使自身的基因更好更多地传递下去,为最根本最原始的欲望——性欲,做好物质上精神上的准备。这也是人生、也是世间万物生存最本质的意义所在——繁殖下一代。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性欲的生物,还能称之为生物。所以,生命之轮就是性欲之轮。人为万物之灵长,人的性欲也是人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性欲之轮也是人性之轮。⑭
正是带着这种理解和认识,宁芩写出了《发现华南虎》、《艳遇的夏天》和《魍魉村庄》这些带着肉欲色彩的作品。这些“下半身”作品的诞生,宣告着“头颅”和“胸膛”的彻底沦陷。
⒈《发现华南虎》:兽性的端倪
其实,很难把《发现华南虎》归为兽性写作,宁芩写这篇小说的初衷更多是对官场和现实以及对人性的讽刺和批判,而且它的写作意图清晰,不像《艳遇的夏天》和《魍魉村庄》那样观点暧昧不清。
在《发现华南虎》中,作者是以狂欢化的形式操作,以油滑的语言风格,以高度的主体介入进入到文本内部,让思想的睿智光芒闪烁,很好地完成了“文以载道”或者对克罗齐所言的“混化在直觉品中的概念”的观念负载。首先,作者拒绝严肃呆板与一本正经,用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等狂欢化所常用的手法,酣畅淋漓地宣泄自己的内心愤怒与不满,已达到强烈讽刺和挖苦的效果。

 从神性到兽性
从神性到兽性  送花(0)
送花(0) 收藏(0)
收藏(0) 喜欢(
喜欢(